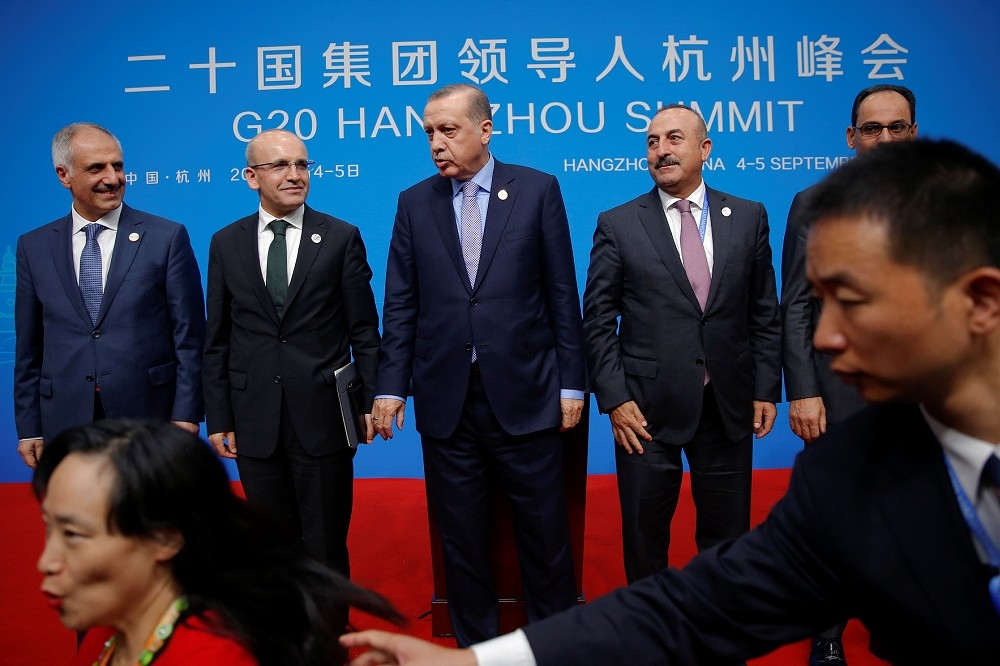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桃園青埔和龜山下午近萬戶突停電 台電致歉:電驛動作跳脫、高壓斷線造成 2024-04-16 20:00
- 最新消息 中東緊張情勢升高 中國有能耐避免全面戰爭爆發? 2024-04-16 19:50
- 最新消息 賴清德視察空軍 了解接戰及防空演練 2024-04-16 19:47
- 最新消息 【寶林茶室中毒】4重症1人已換肝 28輕症皆出院返家 2024-04-16 19:30
- 最新消息 見賣偷拍片好賺 「創意私房」會員自立門戶設立「觸感論壇」 2024-04-16 19:25
- 最新消息 《波拉西亞戰記》三大遊戲核心系統正式公開,開創前所未有玩法! 2024-04-16 19:09
- 最新消息 【懶人包】5月要報稅了 如何申報、稅額計算、免稅族群一次看 2024-04-16 19:02
- 最新消息 徐巧芯曝錄音檔大姑老公稱「要殺我們全家」 卓冠廷:出來社會混遲早要還 2024-04-16 19:00
- 最新消息 卓內閣這麼「男」 婦團提醒賴清德兌現內閣女性三分之一承諾 2024-04-16 18:35
- 最新消息 【有片】哥本哈根證券交易所慘遭祝融 著名17世紀建物毀於一旦 2024-04-16 18:30
在屍速列車上 你被排除了嗎

屍速列車也是社會的縮影。(照片摘自網路)
「社會將不幸的人看作自己的敵人,而不是把不義看作敵人。不幸者不論有罪或無罪,只要一出現,就遭到驅逐判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全責,只因為他沒有在生活中找到一個更好的位置。」(G.Simmel)
「屍速列車」是一部讓人沉重到喘不過氣的影片,片中的列車正是社會的縮影,病毒從最骯髒,最底層,最沒有教育,充滿罪惡與貧窮的地方開始擴散,但這病毒擴散的元兇,卻是金錢遊戲下的資本家 ; 而身染病毒的這群人,代表社會底層的絕對弱勢,但本片將他們化為僵屍,使他們成為絕對的強者,他們不再恐懼,沒有疲累,從底層一路往上追殺前方安逸的人類,而前方的人們因著面對「異己」而產生極大恐懼,所有良知與理性,逐漸瓦解,並對從僵屍群中殺出重圍的生還者,進行污名化並加以排除,呈現比僵屍還醜陋的「惡」。
比僵屍還醜陋的惡
全球化下多元的權力擁有者(資本主義、國家法律、社群輿論、媒體等)對於社會展現了排除性邏輯。它使我們免去對弱勢者的責任,並將諸如貧窮、失業、犯罪等問題歸咎給個人及其家庭,卻怠於反思社會的責任。全球化引發特權與剝奪、財富與貧窮等問題,這樣的兩極化發展,以興盛的資本主義為主,使強者越強,弱者不斷陷入貧困底層,貧窮、犯罪問題層出不窮,最終導致社會排除的產生。
這輛看似明亮有秩序的新自由主義列車,承載了高階人士,也承載新貧族群:單親家庭(秀安和父親)、無家可歸者(流浪漢)、為了降低失業率而造就的低薪貧窮人口(摔角大叔)以及青年人。而快速蔓延的僵屍,則是被排擠到社會邊緣,亦是阿岡本 (Giorgio Agamben)所指,僅剩名字與身體等殘餘價值社會最低階層之「神聖之人」。 神聖之人 (Homo sacer)是羅馬法中的刑法概念。古羅馬法律中,拉丁文的sacer本指任何從普通事物「分別」出來的事物,亦包括神聖和被詛咒的,因此,Homo sacer代表被社會驅逐並剝奪權利的一群人。
「排除」來自於差異性下的恐懼
在「屍速列車」中的僵屍們, 正就是現代社會中被排擠到最底層的神聖之人。在資本主義的消費社會中,為了擠身至主流階級,我們必須層層包裝自己,維持自我形象與社會地位,就像片子一開頭,列車服務員被要求衣著的完美,或是年輕男學生即使面對心儀的學妹,卻依然故作矜持;我們被教導不能輕易的顯露我們的缺點與慾望。相較之下,我們在深層心理中極度羡慕社會底層人士其脫離規範而自由生存的生活形式,但同時也毫不容情地驅離他們,因為他們毫無顧忌的「強」會對主流社會與掌權者帶來威脅與恐懼,迫使掌權者對其污名化並進行驅逐與隔離。電影中營運長恐懼秀安一行人沾染來自貧窮與犯罪的病毒,以及面對他們殺出重圍進入車廂後的污名化,正呈現強權的支配能力受到威脅時所隱藏的恐懼。
因此,我們可以說,「排除」來自於「差異性下的恐懼」。當社會意識到有另一種人,他們的行為會威脅並動搖我們原本固有的地位與價值時,我們會將其視為「異己」,並運用各種符號為其貼上標籤,藉由負面形象的塑造以及隔離,來穩固一般大眾所承認的價值,再經由權力的運作,讓話語權和解釋權回到「正常人」的手裡,接著再更進一步的進行空間與非空間的隔離與排除,來更加具體地展現這個事實。
秀安終究是孤獨的
因此,在影片中,導演已非常明確地表達,想要藉著所有人都往資本階級的門擠進去而得到救贖已是枉然,主流社會對於差異的邊緣化與妖魔化,只會帶來更強大的暴力與報復。前方的門已關上,另一個不被排除的道路,就是回過頭去,共同咬破傷口,接受感染,快速且大量的創造更多的活屍。

然而,在一片血流成河中,影片裡有一雙不同的眼光。在小女孩秀安清澈的眼睛裡,永遠看群體利益大過於個人利益,沒有階級的區分,每個人的生命與權利都值得尊重與保護。秀安勇敢地譴責自私的個人主義,說出那些被社會輕視已久的道德信念與家庭價值,對眾人提出了不同的問題: 社會該是什麼樣子?正義是什麼?當社會成為一個共融的場域,共同分享資源,讓階級流通減少差異性,才有可能不再排除異己。
只是,秀安終究是孤獨的,她的身影單薄且微弱,攙扶著身懷純淨生命的孕婦,流淚唱著宛如對過去道別的驪歌。舊社會已毀滅,只剩一具具行屍走肉永無止盡的漂泊。漫長的隧道後,沒有病毒與政府,軍隊掌管了一切 ; 在全新且陌生的城市,秀安最後是否終於能回到母親的懷抱?孕婦是否順利產下新生命?導演沒有給觀眾答案。不再會有舊列車駛進釜山,而我忍不住地想像,在未來的那日,從釜山重新出發的第一輛列車,將要往哪裡去?
※作者為國家交響樂團小提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