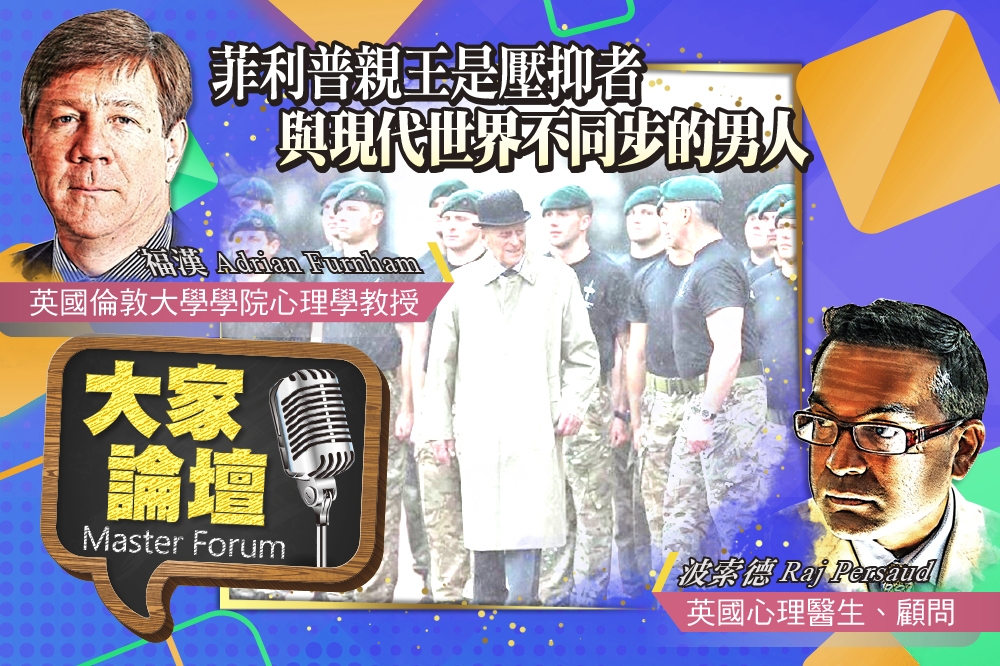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新聞分析/廢死釋憲結果如何繞過民意 將成賴清德首道執政課題 2024-04-23 22:40
- 最新消息 【火藥對槓】不滿法務部牽拖民意反廢死 詹森林連珠炮犀利問「難道要大法官捨棄憲法價值?」 2024-04-23 22:30
- 最新消息 【有片】西班牙增購NASAMS防空系統 提升反飛彈、空防能力 2024-04-23 22:00
- 最新消息 美擬祭終極手段制裁中國銀行 切斷北京助俄發展軍工業 2024-04-23 21:00
- 最新消息 賴清德內閣名單一次看 國安局長、陸委會主委待揭曉 2024-04-23 20:30
- 最新消息 布林肯將訪中談台海情勢 美眾議員籲表達支持和平穩定立場 2024-04-23 20:22
- 最新消息 北市又停電! 捷運昆陽站一帶停電半小時 2024-04-23 20:05
- 最新消息 不斷餘震加上天候差 花蓮秀林2部落強制預防性撤村80人安置 2024-04-23 19:58
- 最新消息 《天堂REMASTERED》全新狩獵場「傲慢之塔地下神殿」將於4/25正式開啟 2024-04-23 19:55
- 最新消息 【最嚴重犯行攻防】殺人罪證確鑿判死違憲? 《羅馬公約》4大罪「比鄭捷案嚴重都未處死」 2024-04-23 19:55

蓋莉
●世界銀行資深經濟學家
卡爾斯
●瑞典巫普薩拉大學傳染病教授
世界衛生組織在組織去年的世界抗生素意識周的時候,將活動的焦點從抗生素擴大到所有抗菌藥——包括抗病毒、抗真菌和抗原蟲藥物。世衛說,在廣義抗生素抗藥性(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 AMR)議程(包括愛滋病和瘧疾)中界定抗生素生物抗藥性(antibiotic resistance , ABR)應對措施能「促進務實的協同和效率,催化國家級行動對抗抗藥病菌(drug-resistant infections)」。但是,ABR和AMR之間固然有著諸多共同之處,但也存在重要區別,必須對抗生素給予特殊關注。
ABR是一場進展緩慢的疫情,部分地受到對落實國家行動(包括成立資源充足的監控體系)的政治支持相對較弱的助長。結果導致缺乏具體環境下抗生素健康和經濟負擔的資料,形成了政策行動障礙。
儘管全球AMR負擔總數字是存在的——最常用的數字是2014-16年間由經濟學家奧尼爾(Jim O’Neill)的英國獨立AMR評估,該評估認為每年造成70萬人死亡——但它們並沒有展現ABR問題,因為覆蓋的細菌範圍有限。事實上,估算表明,光是ABR每年就要造成75萬多人死亡,死亡人數最多的很可能是最貧窮國家的兒童。在一項最新全球調查中,過去五年,79%的新生兒疾病醫生報告了多重藥物抗藥性細菌存在增加趨勢,54%將ABR列為治療新生兒敗血症失敗的主要原因。
在過去,抗藥性問題通常通過研發新抗生素解決。但是,研發固然是ABR應對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它在科學上非常困難,也很昂貴。事實上,藥物開發和抗藥性之間已經形成軍備競賽。在新研發抗生素數量稀少的情況下,我們需要激勵研發,同時讓投資回報與銷售量脫鉤,以延緩抗藥性的演化。
與此同時,上市新藥必須讓所有需要者能夠平價獲得。因進入第二線治療(second-line treatments)而增加的抗藥性中位總成本可能是巨大的,高達每位感染者700美元。在個人帳戶自費額占總健康支出的55%的脆弱國家,這可能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包括發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以及長期貧困。
ABR的健康和經濟成本必須進行量化,以說服政府干預,提高開發抗生素的激勵。這反過來又能論證投資和公私合作促進新藥上市的合理性。
ABR似乎正在贏得這場軍備競賽,這一事實讓捍衛現有抗生素變得更加重要。但在這方面不存在萬靈丹。比如,許多國家急需提高藥物普及度以降低不必要的細菌感染發病和死亡。對抗愛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全球基金等專案部分地解決了有效的抗反轉錄病毒(antiretroviral)、抗結核菌(anti-TB)和抗瘧疾藥物的普及問題。
但一份世衛組織報告指出,「沒有類似的撥款或分配機制應對發展中國家各種普通細菌感染的有效抗生素的需要」。在這一背景下,新成立的多邊信託基金(Multi-Partner Trust Fund)是方向正確的重要一步。儘管該基金的資本規模仍比較小,但它將支持各國實施對抗AMR(包括ABR)威脅的國家計畫。
平衡保護抗生素效果與擴大抗生素普及是一個艱巨的挑戰,因為擴大用量難免會提高ABR。許多窮國的這一問題非常複雜,內戰,拙劣的衛生和營養水準,以及不可靠的供水都有可能導致抗藥病原體的迅速傳播。但問題的總體狀況仍難以獲知,因為缺乏全國監控體系來監控抗生素藥物的使用和抗藥情況。衛生體系方針是至關重要的,它能確保控制ABR的意外後果不會干擾平等而可持續的救命藥物普及。
最近,非洲在這方面有了重要進展。去年9月,非盟各國家和政府領導人宣佈採取共同立場控制AMR。此外,非洲在合作應對COVID-19方面也處於領先,包括推出數位監控和新一代檢測等尖端科技。這些可能成為非洲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AMR監控網路的重要組成部分,該網路旨在連絡人體和動物健康部門的各行動方。這些措施對於非洲特別重要,非洲有許多低收入和脆弱國家可能需要經受AMR的負面後果的衝擊。
日益嚴重的ABR問題不會尊重國界。它本質上是多重系統性失敗的結果,唯有緊急全球集體行動可以克服。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張育軒)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Silent Pandemic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淚之女王》金秀賢逼哭觀眾迎來出道第3次爆紅 寵溺金智媛超甜蜜收視超越《愛的迫降》
- 投書:如果F15EX能加入台灣空軍
- 《不夠善良的我們》林依晨不忍賀軍翔婚姻冷暴力 「簡慶芬出軌」演技大噴發掀淚海
- 最多現省 486 元!拿坡里披薩、炸雞「買一送一優惠」只到月底 12 塊雞腿、腿排只要 399 元
- 《慶餘年》肖戰大學受封校草青澀帥照曝光 他因「這理由」不敢發自拍全網笑翻
- 《長月燼明》白鹿新劇搭檔《蓮花樓》曾舜晞爆不和 他「妝造醜翻」疑遭打壓粉絲氣炸
- 《去有風的地方》劉亦菲現身LV大秀「裙子像鋼刷」遭群嘲 卻因這理由反轉負評好感狂飆
- 麥當勞買一送一!10 塊麥克雞塊、薯餅、焦糖奶茶通通有 歡樂送買一送一、深夜食堂享 79 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