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前委員蕭祈宏涉任詐騙集團顧問被起訴 NCC遺憾:打詐勿枉勿縱 2024-04-16 17:32
- 最新消息 《淚之女王》金智媛、金秀賢相戀又甜又虐超催淚 她曾對「這位男神」動心內幕曝光 2024-04-16 17:30
- 最新消息 唐鳳無緣續任!進入政壇8年 從「天才IT大臣」到爭議不斷 2024-04-16 17:25
- 最新消息 【有片】習近平見蕭茲:中國出口電動車等產品有助緩解全球通膨 2024-04-16 17:25
- 最新消息 自爆其他陣營頻招手卻落腳基隆 楊寶楨嘆:政治圈有太多肅殺 2024-04-16 17:00
- 最新消息 羅雲熙新劇18套造型曝光超吸睛 黃金戰甲上身霸氣超越《長月燼明》 2024-04-16 16:50
- 最新消息 黃曙光向蔡英文請辭國安會諮委、潛艦小組召集人 黃珊珊證實 2024-04-16 16:50
- 最新消息 個人形象爭議太大 川普封口費案審判首日選不出陪審團 2024-04-16 16:36
- 最新消息 高雄國中棒球隊學長「賞巴掌、踹下肢」霸凌學弟 教育局啟動調查輔導 2024-04-16 16:25
- 最新消息 永慶房屋贊助113年全中運賽事 台北市政府頒贈感謝狀 2024-04-16 16:25

穆勒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
●柏林高級研究所研究員
全球自由派開始敢於希望川普總統生涯的暴力結局中孕育著一絲希望,首席教唆犯黯然退出政治舞臺將懲罰其他國家的極權主義民粹主義者。不幸的是,這樣的樂觀是天真的。
與最近民粹主義「風潮」席捲世界的陳詞濫調相反,民粹主義領導人的興衰通常不會造成重大跨國效應。就像小偷總是見不得人,所謂的民粹國際(Populist International)也並不存在團結。川普的同流,如印度總理莫迪、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和俄羅斯總統普京,最終都承認了拜登的選舉勝利。
更重要的是,儘管川普無孔不入,但他從來不是典型的民粹主義者。政府中的右翼民粹主義者,在保持表面的合法性、避免與街頭暴力扯上直接關係方面會更加小心翼翼。1月6日美國國會大廈風暴清楚地暴露了絕望之情,因為未必是其他國家民粹主義(和激進右翼)運動命運的預兆。唯一真正的要點是,如果其他民粹主義當權派真正感到擔心的話,也可能訴諸暴力街頭動員。
自由派常自稱坦然接受世界的複雜性,而民粹主義者把一切簡化。但推動高度簡化的全球民粹主義風潮敘事的也是自由派,好像根本不必仔細考慮特殊的國家環境似的。
根據這一多米諾理論——民粹主義者本身也強烈支持它——2016年川普的意外獲勝據說觸發了奧地利、荷蘭和法國的右翼民粹主義者的勝利。事實上,情況正好相反。在奧地利,極右翼的自由黨(Freedom Party)總統候選人霍費爾(Norbert Hofer)敗選,他採用的川普式的惺惺作態讓他看上去絲毫沒有總統的樣子。在法國。勒龐(Marine Le Pen)在2017年大選中輸給馬卡洪,確認了早已明確的形勢:歐洲川普主義是一個毫無效果的策略。
毫無疑問,一種政治文化中管用的東西,到了其他政治文化未必管用。還有很多東西取決於本身不是民粹主義者的行為人的決定:在美國,川普得益於建制派保守精英與共和黨的勾結。事實上,除了義大利也許是個例外,西歐和北美沒有一個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取得所謂的中右翼行動方的刻意支援的情況下掌權。這些中右翼行動方大多從未因為他們在導致極右翼主流化中所起的作用而受到問責。
此外,即使與右翼民粹主義有關的政黨和治理風格最終互相模仿,也不能得出各地民粹主義者的崛起原因相同的結論。這種相似性的更有可能的解釋是民粹主義領導人有選擇性地彼此學習。
比如,通過看似中立的立法修訂施壓令人討厭的非政府組織是如今標準的民粹主義操作。在一些觀察者所謂的 「專制法律主義」中,許多右翼民粹主義掌權者刻意遵守形式規則和實踐,以保持表面的中立性,粉飾政治行為。和川普不同,這些領導人明白,不受控制的運動所煽動的街頭暴力可能反噬,不管是在本國還是在國際上。
甚至在暴力實際上得到鼓勵的國家——如印度執政的印度教民族主義人民黨對穆斯林的迫害——莫迪這樣的人物也會小心翼翼不留下可解讀為赤裸裸的煽動的隻言片語。類似地,匈牙利政府不停宣傳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但其總理歐爾班小心翼翼地絕不明言,唯恐危及到他與德國基督教民主黨和德國汽車行業的至關重要的關係。
誠然,被逼到絕境的話,任何民粹主義者都有可能訴諸川普的困獸猶鬥:試圖迫使精英做出欺詐行為以防權力轉移,或用右翼極端分子恫嚇立法者。這些絕望的行為暴露了川普的弱點。但必須注意,大部分共和黨仍然沒有與川普割席,即使他在1月6日公然踐踏法律。
其他右翼民粹主義者可能關注到了這一事實。最近美國發生的事情表明,準備與極權主義者合作的精英,最後也很能忍。這一可恥的先例尤其可能在裙帶資本主義與公司非法行為沆瀣一氣的國家成立。
比川普更聰明的民粹主義者用法律和憲法詭計慢慢扼殺民主。但糾合了大企業和盲從的右翼民粹主義當權派,用印度記者科米雷迪(Kapil Komireddi)的話說,不會靜悄悄地下臺。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張育軒)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All Quiet on the Populist Front?》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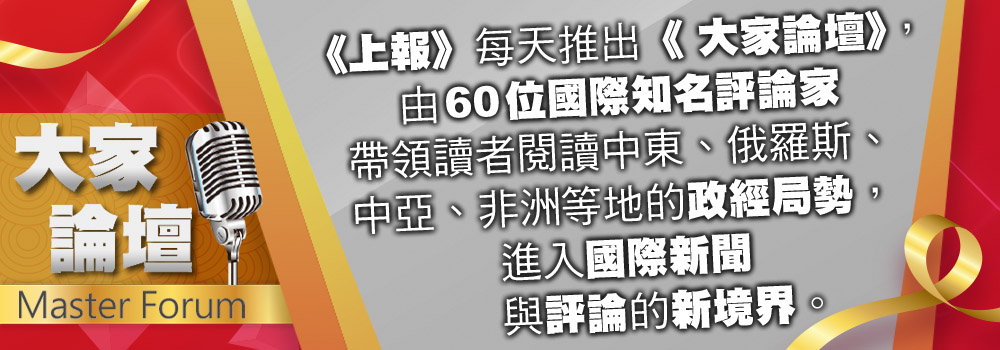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譚松韻新戲戀上《異人之下》侯明昊 她高馬尾造型曝光重現《錦衣之下》少女模樣
- 【潛艦國造案】後續7艘艦預算暴增逾2800億 比海鯤號貴88億嚇呆國防部
- 《去有風的地方》李現秘戀女網紅人氣暴跌 2部新劇與任敏、周雨彤談情搏翻身
- 【《承歡記》內幕曝光】楊紫片酬拿2億演技卻被罵翻 許凱演霸總9千萬輕鬆入袋
- 《蓮花樓》成毅新劇高馬尾造型曝光帥翻 憑2關鍵奪回藝名聲勢輾壓師兄任嘉倫
- 《淚之女王》金智媛、金秀賢互飆演技收視破20% 「洪海仁墓碑」劇照瘋傳網憂BE結局
- 【韓星片酬大公開】金秀賢拍《淚之女王》因「這理由」降價演出 IU身價輾壓宋慧喬
- 《與鳳行》林更新公開女友惹怒CP粉 趙麗穎親上火線17字幫忙救場超暖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