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阿塞德軍隊為何潰不成軍 23歲士兵坦承:我把手機轉「飛航模式」棄槍逃跑 2024-12-13 11:31
- 最新消息 《蜀錦人家》譚松韻激吻鄭業成甜翻播放量破2億 他被抓包「親到滿臉漲紅」全網笑翻 2024-12-13 11:30
- 最新消息 行政院「霸凌通報平台」今天上線 3天內回報、1個月內要結案 2024-12-13 11:21
- 最新消息 避談是否舉行軍演 中國國防部發言人重彈「打獨不手軟」老調 2024-12-13 11:05
- 最新消息 高雄女騎士遇「野狗竄車道」慘摔車 再遭後方機車撞上送醫不治 2024-12-13 11:03
- 最新消息 嚴德發視導花東榮院為AI管理中心揭牌 讓偏鄉醫療智慧化 2024-12-13 10:57
- 最新消息 Capcom 宣布 2026 年推出《鬼武者》系列新作《鬼武者 Way of the Sword》 2024-12-13 10:38
- 最新消息 【雙城論壇】上海台辦主任、9中媒記者遭陸委會封殺 蔣萬安:很遺憾 2024-12-13 10:36
- 最新消息 科技巨擘加緊修復關係 WSJ:亞馬遜擬捐100萬美元給川普就職基金 2024-12-13 10:28
- 最新消息 全台再降溫!明起又濕又冷下探10°C 「這天」有機會下雪 2024-12-13 10:20

1000x80_13.jpg)
1000x80_2.jpg)
塔魯爾
• 印度前外交部長
• 聯合國前助理秘書長
• 現任印度國大黨籍議員
把不同國家領導人做比較往往不明智。但是,儘管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比印度總理莫迪( Narendra Modi)早11年執政,他們的個人、職業生涯的許多特點卻使人無法不比較。
艾爾多安、莫迪都來自卑微的小鎮:艾爾多安曾在李澤省的街道上出售糕點和檸檬水;莫迪則在瓦德納加爾鐵路站幫助父兄經營一家茶攤。兩者都是自我成就的男子漢,體魄強健、精力充沛—艾爾多安在從政前曾經當過足球運動員;莫迪則到處吹噓他56寸胸圍—更不要說他是善於雄辯的演說者。
同聲讚頌歷史成就、欲回復過往輝煌
艾爾多安和莫迪在成長期間都信奉某種宗教信仰,這種宗教信仰成就他們的政治生涯。艾爾多安的正義與發展黨(AKP)、莫迪的印度人民黨(BJP)都宣揚某種帶有宗教色彩的民族主義信條,他們都認為這樣的民族主義信條比,曾影響國家發展指導方針的西方思維更加真實。
為贏得權力,艾爾多安和莫迪並不完全依賴教派選民。兩者都依照現行體制展開競選,欲推動有利於企業政策、減少腐敗政策,認為可以帶來比他們所要取代的現行體制更大的經濟榮景。
為此,艾爾多安和莫迪將過去和未來都為己所用。艾爾多安讚美奧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的遺產,同時告訴選民他們不僅在「選擇總統和代表」,而且在「為國家即將到來的世紀做選擇」。
同樣的,莫迪也不斷回憶古印度所取得的成就,並稱以創造更美好未來的名義重塑古印度曾經的輝煌。
艾爾多安和莫迪為鞏固了自己的力量,透過讚頌過去同時把自己塑造成充滿活力、未來性的改革者—英雄跨著白馬、舉起寶劍,用快刀斬斷阻礙國家前進的亂麻。
善用宗教沙文主義、歷史修正主義煽動
同時,艾爾多安和莫迪將自己描繪成政治局外人,也就是長期被國際世俗主義者邊緣化的「真正的」土耳其和印度人的代表。因為上台初期高漲的民眾不滿情緒,民眾非常樂於接受這樣的政治信號。
對根深蒂固的世俗菁英的怨恨,夾雜著宗教沙文主義和歷史修正主義的煽動,促使他們成為廣大內地及二線城鎮中產階級聲音的代表。
當2003年艾爾多安首次當選總理時,全球經濟蓬勃發展鞏固他的地位,促使他大膽地開始對土耳其政體進行改革。他的政治改革良方—由宗教認同、勝利的多數主義、超民族主義、日益強勢的威權主義(包括體制主導)、對媒體的限制、強勁的經濟增長以及引人矚目的個人品牌所構成的強勢混合因素—使他兩次連任總理,並在2014年成功當選總統一職。
無論是否有意,莫迪在重塑印度的努力中都採用艾爾多安的政策改革良方。他竭力強化印度教沙文主義並推動穆斯林邊緣化。少數民族常常感到困惑,因為莫迪的民族主義不僅排斥他們,而且將他們描繪成叛徒。
在印度政治忠誠可被金錢收買
此外,在莫迪執政下的印度,政治忠誠往往可被金錢收買,以效力於狹隘宗派主義。媒體和大學的持不同政見者均遭到恐嚇。莫迪陷入困境的唯一領域是經濟成長,因為他所領導的政府在經濟管理方面犯下了嚴重的錯誤。
在國際舞台上,艾爾多安和莫迪的行為方式有很多相似之處。兩位都奉行提升國內形象的積極外交政策,並充分利用了散居海外的支持者。
艾爾多安在巴爾幹的講話可能會惹怒歐洲和美國,甚至包括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但這樣的言論卻提高土耳其人對他的支持度。當莫迪在出訪期間面對體育館裡座無虛席的印度僑民講話時,他的演講其實是瞄準印度國內民眾。
土耳其分析家、出版有關艾爾多安書籍的作者卡佩塔葛(Soner Captagay)不久前曾表示,「國內有一半人恨他,認為他做什麼都錯。但卻有另一半人愛他,認為他做什麼都對。」莫迪在印度也屬於同樣情況。
當然了,土耳其、印度有很大的不同之處。土耳其人口為8100萬,還不到印度北方邦2.1億人的半數。土耳其人口中98%是穆斯林,而印度僅有80%的印度教徒。就像印度沙文主義者一直不厭其煩地指出的那樣,與印度教不同,伊斯蘭教是一種全球現象。土耳其沒有聖雄甘地,甘地的非暴力及不合作理念深入在印度每個小學生的腦海中。
印度人不信會步上土耳其後塵
此外,土耳其基本上是已開發國家,而印度要成已開發國家還有一段長路要走。而與印度不同,土耳其未遭過殖民,也從未像印度分裂出巴基斯坦那樣因為宗教的原因而解體過(儘管伴隨土耳其從希臘分裂造成的人口流動具備一定的相似度)。
土耳其曾經歷過軍事統治,而印度卻從來沒有。事實上,印度的民主已經根深蒂固,這加大了單一統治者掌控印度的難度。這部分解釋了為什麼許多印度人很難想像他們的國家會步土耳其的後塵,最終演變為獨裁者執政的多數非自由民主制度。
儘管莫迪及其印度人民黨確實尚未達到,艾爾多安與正義與發展黨那樣的「國家控管程度」,但他們還有11年的路要走。莫迪所走的道路相似到足以與艾爾多安進行比較—並引起人們關注。
警鐘正在敲響:像土耳其里拉一樣,上個月印度盧比也貶值超5%。在兩國即將舉行大選之際—土耳其在這個月,而印度在2019年春天—選民會不會聽到警報?
(原標題為《The Modi-Erdoğan Parallel 》,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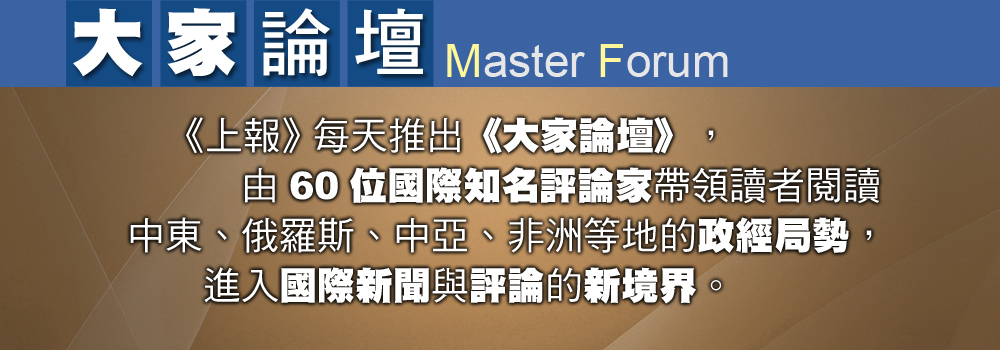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趙麗穎與《玫瑰的故事》林更新爆熱戀 她帶兒子看煙火他「這穿搭」現身放閃
- 趙麗穎與《玫瑰的故事》林更新被抓包穿情侶裝 兩人隔空示愛3證據曝光全網沸騰
- 張若昀《慶餘年》第二季流量奪冠成劇王 他開2千萬跑車因「這舉動」形象全毀
- 【有片】中華隊球員「無敵星星」吊飾哪裡買?博客來明日早上再次開放預購
- 《長相思》檀健次開唱勁歌熱舞嗨翻 卻被抓包在台上做「這件事」超噁心掀罵聲
- 《永夜星河》虞書欣新劇停拍3天劇組全換人 官方海報獨厚她卻沒男主角內幕曝光
- 譚松韻《蜀錦人家》與鄭業成吻戲被刪光掀眾怒 2敗筆熱度慘輸孟子義新劇《九重紫》

1000x20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