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阿里山翊悅號 5 月首航!全台唯一彩繪登山火車搶先看 零死角瞭望席嚐海拔最高下午茶 2024-04-25 10:00
- 最新消息 台中「御帝和牛」燒肉囤逾百公斤過期肉遭檢方約談 臉書IG一夜消失 2024-04-25 09:59
- 最新消息 直播/卓內閣第6場人事發布 10:00預計公布國安首長 2024-04-25 09:50
- 最新消息 母親節用餐送祝福花禮!《繁花》主角最愛的「排骨年糕」、「紅燒肉」樂天皇朝吃得到 第二道享 72 折優惠 2024-04-25 09:00
- 最新消息 習近平訪歐前夕下馬威? 歐盟突襲中國國營安檢設備廠「同方威視」 2024-04-25 08:50
- 最新消息 【有片】拜登簽署TikTok「不賣就禁法案」即時生效 周受資嗆告到底 2024-04-25 08:30
- 最新消息 【有片】布林肯遊上海看籃球賽 拍片誓言解決芬太尼等美中分歧 2024-04-25 07:50
- 最新消息 Studio Colorido 動畫電影《我的鬼女孩》5 月網飛上映,由「永遠是深夜有多好。」演唱主題曲 2024-04-25 07:30
- 最新消息 李濠仲專欄:習近平看到這張照片會怎麼想台海100年後 2024-04-25 07:00
- 最新消息 《大家論壇》止戰視角:確保區域停火 緩和中東局勢機會之窗 2024-04-25 07:00

1000x80_10.jpg)
1000x80_8.jpg)
柯尼格
●法國哲學家
●法國智庫「自由世代」的創始人兼主席
從11~13世紀的中世紀盛期,法國的農民沒有財產權。相反的,那些有土地的人不得不將他們生產的大部分東西上繳給當地的領主,領主可以在農民去世後沒收他們的土地。
作為回報,農民確實獲得如免遭侵襲、使用磨坊或鄉村公共烤麵包房等服務。不過,他們事實上別無選擇,例如,建造自己的磨坊是被嚴格禁止的。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法國大革命爆發,農民獲得完整產權為止,而且看起來很像當今消費者、網路業者間關係。
現在我們所處的數位封建主義時代,並沒多少選擇,只能點擊同意那一串密密麻麻的冗長、複雜條款條件,將自己置於所使用網路平台監控之下。這些平台收集我們個人資料,將其出售給其他人,包括那些可以為我們提供針對性廣告的廣告公司。
使用者個資市場將達歐洲GDP的8%
對於網路公司而言,這是獲利豐厚的做法。到2020年,使用者個人資料的市場規模預計將相當於歐洲GDP的8%。這些業者向不斷生產資料的數位農奴提供社交媒體等「免費服務」以作為交換。
這不是一個「共享經濟」,而是一個被優化過的採掘經濟,是犧牲消費者為代價來養肥少數公司,而使用者的個人資料近乎是無限的。就像中世紀盛期的經濟一樣,透過產權進行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幾千年來,財產權一直在保護並賦予人們權力,隨著技術發展而不斷演進。例如,印刷革命催生智慧財產權——這要感謝博馬舍(Beaumarchais);工業革命推動專利制度普及。
而數位革命必須帶來個人資料所有權,裡面包括財產權的經典拉丁文要素:usus(使用權,即我按照自己的意願使用自己的資料)、abusus(處分權,即我按照自己的意願銷毀我的資料,無須借助任何形式的「被遺忘權」)、fructus(孳息,即我可以自由出售自己的資料獲利)。
35億網路用戶需更有個資所有權概念
個人資料所有權將催生出個人資料市場,在全球35億網路用戶中,有些人會要求依據他們分享的資料所產生的價值支付報酬,而其他優先考慮隱私而不是利潤的客戶則會支付公平的市場價格以匿名方式從服務中受益。這就是美國科技企業高階主管,如臉書(Facebook)營運長桑伯格(Sheryl Sandberg)最近所暗示的狀況,當時她建議將全面避免臉書進行資料收集的選項列為「付費產品」。
這種變化將是深遠的,而現實的各類挑戰可以通過現有技術解決方案來克服。舉例來說,為了支援資料管理,每個使用者可以擁有一個「智慧帳戶」,用於儲存資訊與其用途的合約條件。至於定價,中間商可能會代表數百萬用戶直接與大平台進行談判,從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創建一個恰當運行的市場。
在個人資料所有權方面的有效法律執行肯定會起作用。然而,與提出的其他手段相比(例如德國憲法法院於1983年制定的「資訊自決權」),個人資料所有權仍然是一種更為理性和現實的解決方案。
讓個人具更多控制數位生活的潛在好處會超越到經濟公平性之外。這樣的系統還可以打破因社交媒體演算法而衍生、備受詬病的「過濾泡沫」,這些演算法會向使用者展示那些強化其現有偏見和信念的內容。從這個意義上講,個人資料所有權可以説明緩解現在困擾許多國家的危險政治極化現象。
尚無法律承認個資所有權
雖然迄今為止,沒有一個法律體系承認個人資料所有權。但這個想法正在全世界範圍內不斷生根。
凱撒(Brittany Kaiser)、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據報該公司濫用臉書和其他平台使用者資料來影響政治活動)的前高管兼告密者,現在主張使用者將自身資料視為財產,就跟自己的房子一樣。
擁有房子不會讓你成為一個貪婪的房地產投機者;而是允許你充分參與到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所謂的「財產所有權的民主制度」當中。資料也是如此。
在法國,我創建的智庫機構「自由世代」(GenerationLibre)發佈一份長達150頁的個人資料所有權報告並引發了激烈的公眾辯論。在歐洲層面,剛剛生效的《通用資料保護條例》通過保證個人資料的可移動性為相關的財產權奠定了基礎。
在美國,作家兼研究者威爾(E. Glen Weyl)以及傳奇的虛擬實境先驅蘭尼爾(Jaron Lanier)等人最近都提出資料應該被視為勞動力(並相應支付報酬)。(不過我本人更願意將資料視為資本,因為它們源於我們的自有人格,但這基本上只是語義上的不同而已。)而且在實際層面上,越來越多的初創公司正在開發資料貨幣化服務。
在他的暢銷書《人神:未來簡史》(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中,歷史學家尤瓦爾·諾亞·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預見到「資料主義」的誕生,即在演算法的祭壇上犧牲個人自由意志。人類其實不必受資料流程的支配。透過確立個人資料所有權,個性的具體概念可以得到強化,並推動那些使我們的文明實現繁榮的自由主義價值觀。
(原標題為《Leaving the Data Dark Age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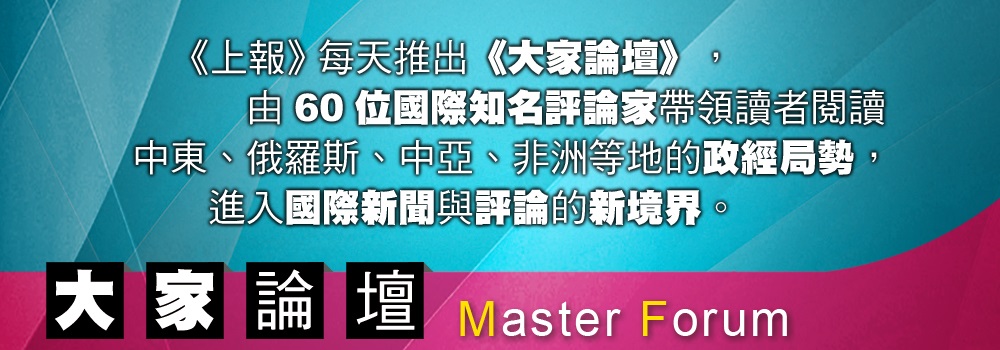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淚之女王》金秀賢逼哭觀眾迎來出道第3次爆紅 寵溺金智媛超甜蜜收視超越《愛的迫降》
- 投書:如果F15EX能加入台灣空軍
- 《不夠善良的我們》林依晨不忍賀軍翔婚姻冷暴力 「簡慶芬出軌」演技大噴發掀淚海
- 最多現省 486 元!拿坡里披薩、炸雞「買一送一優惠」只到月底 12 塊雞腿、腿排只要 399 元
- 《慶餘年》肖戰大學受封校草青澀帥照曝光 他因「這理由」不敢發自拍全網笑翻
- 《長月燼明》白鹿新劇搭檔《蓮花樓》曾舜晞爆不和 他「妝造醜翻」疑遭打壓粉絲氣炸
- 麥當勞買一送一!10 塊麥克雞塊、薯餅、焦糖奶茶通通有 歡樂送買一送一、深夜食堂享 79 折
- 《寧安如夢》張凌赫擠走緋聞女友白鹿成GUCCI大使 新劇與徐若晗花瓣雨下熱吻甜翻

1000x200_8.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