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台南網紅PO「幼童版N號房」控性侵 幼兒園家長怒:遭惡意剪輯 2024-12-14 18:55
- 最新消息 【大巨蛋經濟】人潮帶錢潮、商機撐房價 噪音塞車太惱人 2024-12-14 18:53
- 最新消息 【大巨蛋經濟】北市最大百貨城將臨 東區外溢紅利難保? 2024-12-14 18:52
- 最新消息 【大巨蛋經濟】各縣市跟風搶孵蛋 展演王:市場不大難撐盤,爆熱嘗鮮明年恐到頂 2024-12-14 18:50
- 最新消息 羅文嘉提雙城論壇救一貫道 郝龍斌:海基會溝通到哪去了? 2024-12-14 18:25
- 最新消息 遭彈劾後首度發聲 尹錫悅強調「永不放棄」、「為國家盡力直到最後」 2024-12-14 18:12
- 最新消息 王鶴棣、田曦薇新劇《大奉打更人》Disney+播出 花絮曝光他拋偶包逗童星溺愛滿溢 2024-12-14 18:01
- 最新消息 勞動部公務員遭霸凌輕生 家屬淚謝:感謝讓真相水落石出 2024-12-14 17:52
- 最新消息 即刻開始代理總統職務 南韓總理韓悳洙是何人 2024-12-14 17:35
- 最新消息 陸軍向美採購首批38輛M1A2T戰車 預定15日深夜運抵台北港 2024-12-14 17:20

德維斯
●土耳其前經濟部長
康羅妮
●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分析員
做為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標誌性民族主義大旗背後的核心理論家,巴農(Steve Bannon)2018年對歐洲廣泛訪問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巴農現在想在歐洲建立一個民族主義政黨聯盟。不過,人們也懷疑一個打造「美國優先」理論的人該如何在美國之外的地方追求其政治抱負。
透過與法國極右翼領導人勒龐(Marine Le Pen)聯手—此人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公開支持者—巴農似乎構思出一種新型「新民族主義國際(neo-nationalist international)」。
民族主義獨裁國家暴增
隨著愈來愈多的國家在強人統治下將自身轉變為民族主義獨裁國家、非自由民主國家,民族主義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公約數。但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應該認真看待「國際化的民族主義」這個自相矛盾體。
從歷史上看,國際主義一直是左派的保留地,最早是法國革命黨人試圖將他們的政治抱負推廣到全歐洲,但卻終結在拿破崙的波拿巴主義(Bonapartist)獨裁統治中。但有趣之處在於倘若當年那些歐洲意識形態接受國走上了帝國共和主義道路,情況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在上個世紀初,社會主義國際主義比其前身在實現其全球野心方面更為接近。這一社會主義運動牢牢紮根於古典馬克思主義,將民族國家視為實現無產階級普世主義的暫時載體,大多數國家最終會在國際框架下實現共產主義,民族國家將最終消亡。
當時,像盧森堡(Rosa Luxemburg)這樣的共產主義領導者——甚至某一段時期的列寧(Vladimir Lenin)——都相信共產主義制度首先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找到立足點,然後擴散至世界各地。
隨著俄羅斯帝國的崩潰,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開始將蘇聯設想為全球共產主義的先鋒。但當歐洲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革命相繼失敗後,史達林(Joseph Stalin)、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對蘇聯的歷史任務進行了重新思考,就是要去建設「一個國家範圍內的社會主義」。
蘇聯本身最初被設想為一個受雙重制度架構駕馭的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一邊是由典型部門組成的官僚機構,另一邊則是共產黨。在這種安排下,各級黨委形成了一個平行的權力結構並向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報告。
新興國家加入西方主導國際秩序
理論上,聯邦內各個共和國地位對等,俄羅斯民族主義受到壓制。實際上是俄羅斯統治著其他國家,因為它是權力的所在地。
蘇聯在經濟方面並不存在明確的民族主義——保護主義政策。然而,由於生產是由莫斯科集中規劃的,經濟政策制定實際上發揮了保護主義作用,導致國內出現不對等情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幾十年間,歐洲許多共產主義和左翼社會主義反對黨都聽取克里姆林宮的指揮,其中包括分別佔據著各自國家約三分之一選區的法國、義大利共產黨,以及直到1959年拜德哥德斯堡會議(Bad Godesberg Congress)後才正式放棄其馬克思主義根源的德國社會民主黨。
與此同時,西方繼續主宰著世界經濟。美國的帶領下西方國家實現貿易自由化、鼓勵其他國家開放經濟。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獨立新興國家加入西方主導國際秩序,就連中國這個名義上的共產主義國家最終也在追求成的過程中接受西方經濟原則。
此期間的西方民主國家中社會主義在很大程度上被廢棄,取而代之的則是支持自由市場,非中央計畫為資源配置機制的社會民主主義。
巴農在歐洲政黨內沒地位
那麼如何在這個歷史背景下解讀巴農的倡議?他的目標當然不是建立一個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右翼替代品。法國國家聯盟黨的里維埃(Jérôme Rivière)等歐洲主要右翼民族主義者完全拒絕了這一想法。
「巴農是個美國人,在歐洲政黨中沒有地位」,里維埃在7月接受美國雜誌《Politico》採訪時表示,「我們反對任何超國家實體,也沒有參與巴農創建的任何東西。」
可見巴農的使命不是改善政策制定、建立新機構來管理21世紀的經濟和技術挑戰。 相反的,他唯一重點是削弱並在可能的情況下瓦解「自由社會」所取得的成就,例如歐洲的整合。
該整合的核心是巴農及其盟友想要摧毀的兩條國際主義脈絡:一種是自由主義的中右翼,另一種是自由主義的中左翼。而正是這個目標——而非其他任何類似政策——促成了都是歐洲極右翼政黨的聯合。儘管遭到了削弱,但歐洲仍然是自由主義國際主義思想的中心,也正是這一點使它成為了各地民族主義者在意識形態上的眼中釘、肉中刺。
(原標題為《Nationalists of the World, Unite? 》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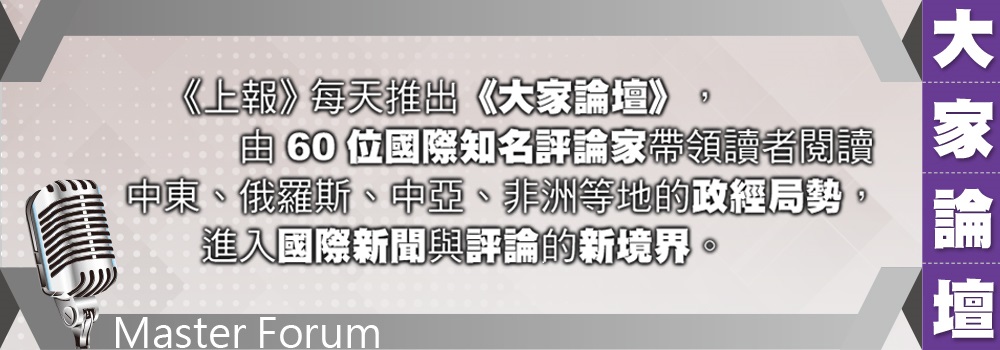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張若昀《慶餘年》第二季流量奪冠成劇王 他開2千萬跑車因「這舉動」形象全毀
- 《繁花》胡歌睽違9年接演古裝劇竟被看衰 網推這位「台灣金馬獎影帝」比他更適合
- 【有片】中華隊球員「無敵星星」吊飾哪裡買?博客來明日早上再次開放預購
- 《蜀錦人家》譚松韻激吻鄭業成甜翻播放量破2億 他被抓包「親到滿臉漲紅」全網笑翻
- 《長相思》鄧為消失10個月沒戲拍原因曝光 新劇與白鹿、楊紫新作對打恐淪砲灰
- 《永夜星河》虞書欣新劇爆金主撤資風波不斷 《偷偷藏不住》趙露思哥哥演男配慘被換角
- 《九重紫》李昀銳演白髮將軍熱戀孟子義 他含冤入獄「這一幕」帥翻全網夢回《星漢燦爛》

1000x80.jpg)
1000x20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