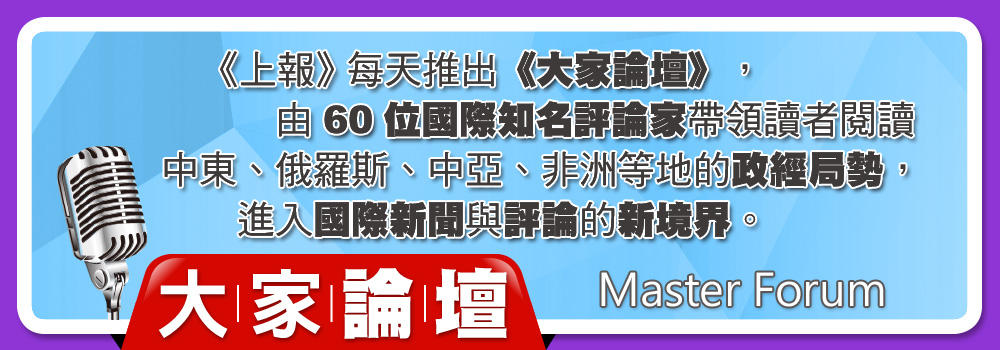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檢方第9度提訊!被問不法所得是否上億 柯文哲未回應 2024-12-11 22:35
- 最新消息 【大法官人事案】難忘被害人家屬絕望神情 王碧芳:我支持死刑 2024-12-11 22:16
- 最新消息 法總理上任僅3個月垮台 馬克宏擬48小時內提新人選 2024-12-11 21:56
- 最新消息 動輒飆罵下屬「混蛋」 數發部2主管涉霸凌降調非主管職務 2024-12-11 21:51
- 最新消息 南韓總統辦公室僅提交小部分資料 警方搜查行動無功而返 2024-12-11 21:28
- 最新消息 陸委會「有條件」放行雙城論壇 北市府:秉持4原則持續交流 2024-12-11 21:14
- 最新消息 【大法官人事案】反對翁曉玲版《憲訴法》 王碧芳:會癱瘓憲法法庭 2024-12-11 20:45
- 最新消息 保護本土產業鏈 美將宣布中國太陽能板關稅提高2倍 2024-12-11 20:41
- 最新消息 「一隻阿圓」穩交陳百祥 眼尖網友:去年就曾一起去韓國! 2024-12-11 20:10
- 最新消息 「入冬最強冷氣團」來襲周末恐剩10°C 中醫推薦「2種養身飲」暖身又暖心 2024-12-11 19:42


錢勒尼
• 印度前國安會顧問
• 現職為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戰略研究教授
• 著有9本專書,包括《亞洲神力:中國、日本與印度的崛起》、《水資源、和平與戰爭:面對全球水危機》等
發生在斯里蘭卡的復活節星期日爆炸是現代史上最致命的恐怖襲擊之一,向世人展示了伊斯蘭暴力運動向亞洲轉移的災難性後果。
激進的伊斯蘭團體,其中部分隸屬於規模更大的極端主義網絡,影響力一直從馬爾地夫到菲律賓群島的一系列國家暗中不斷擴大,而且它們所構成的威脅不能再被繼續忽視。
事實上,可怕的斯里蘭卡爆炸事件提醒人們,不是中東,亞洲才是受恐怖暴力影響最嚴重的地區。
由於基層激進運動的崛起和決策者多年來的驕傲自滿,作為世界絕大多數穆斯林家園的亞洲同時也是多個「恐怖主義避風港(terrorist safe havens)」的所在地。
死亡人數創新高
由於造成359人死亡(以及數百人受傷),斯里蘭卡爆炸事件的致死人數是3月15日紐西蘭基督城(Christchurch)一名白人至上分子,在2座清真寺製造大屠殺事件的7倍。
這次襲擊的死亡人數同時也是2008年孟買(Mumbai)襲擊的2倍,那起襲擊事件涉及10名巴基斯坦武裝分子,也是現代世界有史以來時間最長的恐怖襲擊之一。
透過將襲擊目標對準國際酒店和象徵性教堂,斯里蘭卡爆炸事件背後的伊斯蘭分子顯然意在打擊伊斯蘭卡快速增長的旅遊業,而旅遊業恰恰是斯里蘭卡負債累累的國內經濟的支柱產業。
旅遊收入銳減將加重斯里蘭卡本已嚴重的對外利息負擔,導致現有問題進一步加劇,上述問題已經迫使斯里蘭卡將戰略性印度洋港口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的控制權轉移給中國(這是中國債務陷阱外交所取得的指標成績)。
伊斯蘭教義派
上述襲擊同樣標誌著斯里蘭卡伊斯蘭恐怖活動的開始。
儘管自殺式爆炸事件在該國多數僧加羅人(Sinhalese)與少數泰米爾人(Tamils)長達26年的內戰史上並不罕見,但斯里蘭卡先前從未經歷過如此規模的暴力或伊斯蘭武裝分子的重大襲擊。
內戰以2009年4月斯里蘭卡軍隊殘酷鎮壓最後一批泰米爾分離主義叛軍宣告結束。但這一結果,卻播下了主要信奉佛教僧迦羅人和穆斯林少數族裔(占人口總數1/10)間爆發宗教衝突的種子。
斯里蘭卡的穆斯林人口主要集中在東部省份,沙烏地阿拉伯和其他海灣國家的資金一直在當地協助推行伊斯蘭教法(sharia )聖戰組織的興起。
在這樣的環境下,發展出被外界懷疑製造此次復活節爆炸事件的National Thowheed Jamaath組織。與同名機構Sri Lanka Thawheed Jamaath和在印度最南端快速發展的Thowheed Jamath一樣,組織主要目標均是煽動好戰的伊斯蘭基本教義派(Islamic fundamentalism)。
瓦哈比狂熱主義
現在我們知道,印度情報機構曾向斯里蘭卡安全部門通報復活節爆炸陰謀,甚至明確指出了所謂的幕後主使。但因斯里蘭卡總統西里塞納(Maithripala Sirisena)和總理維克勒馬辛哈(Ranil Wickremesinghe)之間的政治鬥爭,後者完全被蒙在鼓裡。
因此,很多人現在將矛頭對準負責監管安全機構的西里塞納(西里塞納曾試圖發動憲法政變推翻維克勒馬辛哈,惟最高法院干涉才作罷)。
雖然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極端主義化外之地(extremist enclave)」已灰飛煙滅,且領導人正逃亡中,但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IS)聲稱對此次爆炸事件負責。就像之前的基地組織(al-Qaeda)一樣,伊斯蘭國希望透過在從未存在的地區為發動恐怖襲擊事件負責,持續證明相關性。
最有可能的是,斯里蘭卡襲擊並非伊斯蘭國的直接作案,但他們受到伊斯蘭國所擁戴同樣有毒思想的啟發:瓦哈比狂熱主義(Wahhabi fanaticism)。
恐怖主義份子返鄉
由沙烏地阿拉伯和其他海灣酋長國資助的瓦哈比主義是嚴格、僵化版的伊斯蘭教,現在依然是伊斯蘭恐怖主義背後的推動勢力。
其後裔不僅包括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還包括阿富汗的神學士(Taliban)、巴基斯坦的虔誠軍(Lashkar-e-Taiba)、奈及利亞的博科哈蘭(Boko Haram)和索馬利亞的青年黨(al-Shabaab)等組織。
對非遜尼派(non-Sunnis)的敵意和對現代化拒絕所產生的虛無主義憤怒(a nihilistic rage)是上述這些組織背後的驅動力。
不幸的是,就像斯里蘭卡爆炸事件和其他亞洲恐怖襲擊所證明的那樣,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失敗只會進一步加劇恐怖主義難題,因為經過戰爭洗禮且受過行動訓練的戰士們,正返回祖國發動野蠻襲擊。
這些經過訓練的恐怖分子返回斯里蘭卡可以合理解釋,一個不起眼的當地團體如何使用軍用炸藥對三座教堂和三所酒店幾乎同時發動精準度極高的恐怖襲擊。
恐怖主義降臨亞非
從菲律賓、印尼、馬爾地夫和烏茲別克(Uzbekistan),其他許多亞洲國家也出現了回流的恐怖分子。
就像在反對蘇聯佔領阿富汗戰爭中,美國所支持嶄露頭角的賓拉登(Osama bin Laden)和其他基地組織領導人一樣,這些新一代的聖戰老兵可以在未來許多年持續對亞洲、中東和西方的安全構成威脅。
可以肯定,官方對穆斯林的歧視已經促成了伊斯蘭分子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尤其是在緬甸的若開邦(Rakhine state)、泰國最南端的4個省以及菲律賓南部的民答那峨島(Mindanao)等地區。
但產生同樣作用的,還有沙烏地阿拉伯出資興建的宗教學校(宗教神學院)和社交媒體平臺,這些宗教學校和社交平臺促成了與聖戰言論有關的籌款、人員招募和輿論傳播。
因此,聖戰暴力也開始威脅到印尼、馬來西亞、孟加拉和哈薩克(Kazakhstan)等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而且,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巴基斯坦) 政府本身正在慫恿暴力極端分子。
反恐戰失去動力
如果不加以解決,這場災難很可能會成為亞洲國家本世紀的決定性危機。
為防止這樣的後果出現,必須從源頭上切斷聖戰極端主義(瓦哈比狂熱主義),就如已故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所說,預防恐怖襲擊要求我們消滅「蜂王(queen bees,仇恨和暴力的傳道者)」,却讓蜂王激勵「工蜂(worker bees,自殺式炸彈襲擊者)成為烈士。
由美國在2001年911襲擊後發動的全球反恐戰爭正在失去動力,除非這場戰爭恢復生氣並戰鬥到底,否則,只會失去更多無辜的生命。
(責任編輯:簡嘉宏)
(原標題為《Asia Is the New Ground Zero for Islamist Terror》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