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楊紫《長相思》虐戀檀健次、鄧為掀淚海 第二季張晚意冷血復仇埋悲劇結局 2024-04-24 16:33
- 最新消息 大法官問「一定要跟大多數民意妥協嗎?」 國民黨團籲:別和人民對幹 2024-04-24 16:12
- 最新消息 寵物頭套必收!肯德基 × 貓福珊迪第二波聯名周邊加價購亮相 母親節預購享 6 折起 2024-04-24 16:00
- 最新消息 【有片】通用原子「莫哈韋」無人機測試對地掃射能力 全球首隻火焰噴射無人狗問世 2024-04-24 15:50
- 最新消息 爆台北慈濟醫院偷拍病患、揉胸 「吹哨者護理師」手機內存30多張私密照 2024-04-24 15:45
- 最新消息 趙少康怒批「幾個大法官決定廢死沒道理」 拋由公投決定 2024-04-24 15:31
- 最新消息 《繁花》辛芷蕾調侃楊洋「20年不參加綜藝」被炎上忙道歉 他親上火線回應獲讚高EQ 2024-04-24 15:30
- 最新消息 「台灣不是以色列」 馬英九質疑:台海開戰美國會毫無保留挺台嗎 2024-04-24 15:11
- 最新消息 東京君悅推寶可夢主題房!巨型卡比獸陪睡 入住送睡眠寶可夢玩偶 2024-04-24 15:00
- 最新消息 【周末天氣預報】鋒面帶來豪大雨 西半部「紫色一片」未來4天恐溼答答 2024-04-24 14:57


道格
● 漢諾瓦遠期資本公司管理合夥人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教授加布萊斯(James K. Galbraith)近期在《Project Syndicate》專欄中發表的一篇文章,為現代貨幣理論辯護並糾正了對現代貨幣理論、聯邦赤字和央行獨立性之間關係的一些誤解。
但,加布萊斯並未探究一個或許是最重要的問題:有效實施現代貨幣理論所需的政治條件。
現代貨幣理論新發現的這一關聯性其實與通貨緊縮(deflation,而非通貨膨脹)正日益成為央行主要憂慮點的事實有關。對於美國這類高負債高赤字經濟體而言,通貨緊縮是一個特別嚴重的威脅,因為它會延遲消費並讓債務人倍感焦慮。如果預計未來價格會走低,消費者就會放棄大宗採購。
當房價下跌且名下房屋淨值下降時,背負房貸的房主就會削減開支。這些削減令美國聯準會(FED)感到擔憂,因為它們增加了通縮壓力,並可能引發更嚴重的開支削減,股市下跌以及大面積的去槓桿化。
美國聯準會至今無力達到2%年度通膨目標的事實表明該機構缺乏克服經濟中持續通縮力量的手段。
這些力量包括不斷提高的美國市場集中度,因此導致的員工討價還價能力減弱和收入不平等加劇都壓低了總需求;人口老齡化、基礎設施和氣候變化延緩措施方面的投資不足、還有因科技發展導致的勞動力取代。
更糟糕的是,美國的政治僵局導致國家在邁向經濟枯竭的戰略道路上漸行漸遠,比如犧牲教育投資和其他長期為富人減稅。這些條件都迫使美國政府要在支出和稅收政策上推行重大變革。
而現代貨幣理論則被視為實現上述變革的一種方式。
它認為如果政府以本國貨幣借款,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去開銷,同時央行可以根據需要購買盡可能多的政府債務,只要不會產生令人無法接受的高通膨就行了。減稅宣導者和公共投資鼓吹者都打心眼裡喜歡這種理論。
但現代貨幣理論也受到了政治領域左中右各派經濟學家的嚴厲批評,從哈佛大學的(Kenneth Rogoff)和薩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再到紐約城市大學的克魯格曼(Paul Krugman)。
所有人都認為這是一種偽裝成經濟理論的政治論點。但布里吉華特對沖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的加布萊斯和達里歐(Ray Dalio)則對現代貨幣理論的看法有所不同。
達里歐認為現代貨幣理論是真實的,更重要的是,它是歷史上反復出現的債務週期下行階段的必然政策步驟。
達里歐在著作《駕馭大型債務危機的原則》(Principles for Navigating Big Debt Crises)一書中記錄了各央行以往在面對蓬勃發展的經濟體在債務重壓下突然癱瘓時所採取的措施。
第一步(貨幣政策1)是降低隔夜官方利率以刺激信貸和投資擴張。第二步(貨幣政策2)是購買政府債務(量化寬鬆)以支持資產價格並防止失控的去槓桿化海嘯。如果這兩步都不足以阻止經濟衰退,央行將採取第三步(也就是現代貨幣理論,達里歐稱之為貨幣政策3)並繼續為政治領導人認為最有必要的支出事項提供資金。
這些事項可以涵蓋重大國家專案融資或直接轉移到消費者手裡的「直升機資金(helicopter money)」。
如果想有效實施貨幣政策3,就必須針對資助哪些項目以及如何資助達成政治協議。在金融危機或其他國家緊急狀態下,政治團結和迅速行動至關重要。而實現團結需要就應當資助的事項達成強有力的共識,快速出手則要求存在受信任的機構來指導這些支出。
在1940年代早期,當參加二戰並獲勝成為美國政府的首要任務時,美國聯準會進入了完整的貨幣政策3模式。
它不僅設定了國債的短期和長期利率,而且還購買了必要的政府債務以資助戰爭。而貨幣政策3之所以可實現,是因為戰爭在政治上團結了整個國家,並給與了當時羅斯福政府(Roosevelt administration)近乎專制的經濟權力。
而貨幣政策3/現代貨幣理論的核心弱點在於並未解釋在資助哪些物件以及如何資助方面實現政治團結。這種缺失是不可原諒的。美國的債務總額(相對GDP的比率)正接近與過去金融危機相近的水準,這還是在沒有納入與基礎設施維護,海平面上升和缺乏資金的養老金相關的隱性債務的情況下。
鑒於達里歐所提出的原因,一場需要某種形式的貨幣政策3來應對的美國債務危機幾乎是無可避免的。
但任何實現政治團結的努力必須回答的關鍵問題在於什麼才是所謂合理的支出。
美國首任財政部長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在1781年給出了一個答案:「國債,只要不過度,那對我們來說將是一份全國性的大禮(A national debt, if it is not excessive will be to us a national blessing.)」,如果這些國債是以收益不足以增加國家財富的方式來開銷,並無力償還的話,那麼它才是「過度的(excessive)」。
被花在購買豪華遊艇上的減稅額所產生的債務幾乎肯定是過度的;為改善教育成果,維持基本基礎設施或應對氣候變化而產生的債務則可能不會。因此如果將貨幣政策3的收入用於教育,基礎設施或氣候等優先事項,那麼將更容易實現政治團結。
判定貨幣政策3資助下的政府支出是否正當的政治考驗點也相當明確:那就是後面幾代人會否判斷這些借款並未「過度」。
二戰後出生的大多數美國人都說為贏得這場戰爭而背負的債務是合理的,為州際公路體系建設提供資金的債務也是合理的,因為它為更強勁的(經濟)成長奠基。
正如1930年代至1940年代所表明的那樣,貨幣政策3是政府應對重大債務經濟低迷狀況及其觸發的政治危機的自然組成部分。與20世紀上半葉相比,我們對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的促成因素有了更多瞭解。
為了加速從下一次經濟衰退中復甦,吾人現在需要定義對可持續復甦貢獻最大而且將被未來美國人認為最合理的的支出類型,此外,還需要設計構建一批能夠指導這類支出的機構。
這些是建立現代貨幣理論所要求的政治團結的關鍵,如果想知道改為哪些項目融資,以及如何融資,未來的美國人可以為我們指引道路,而我們要做的,則是設身處地地為他們著想(To know what to finance and how, future Americans can show us the way; we need only put ourselves in their shoes.)。
(原標題為《Modern Monetary Inevitabilitie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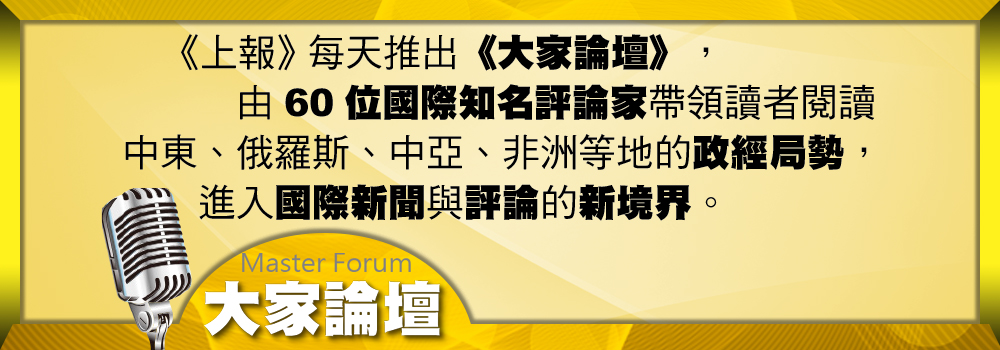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淚之女王》金秀賢逼哭觀眾迎來出道第3次爆紅 寵溺金智媛超甜蜜收視超越《愛的迫降》
- 投書:如果F15EX能加入台灣空軍
- 《不夠善良的我們》林依晨不忍賀軍翔婚姻冷暴力 「簡慶芬出軌」演技大噴發掀淚海
- 最多現省 486 元!拿坡里披薩、炸雞「買一送一優惠」只到月底 12 塊雞腿、腿排只要 399 元
- 《慶餘年》肖戰大學受封校草青澀帥照曝光 他因「這理由」不敢發自拍全網笑翻
- 《長月燼明》白鹿新劇搭檔《蓮花樓》曾舜晞爆不和 他「妝造醜翻」疑遭打壓粉絲氣炸
- 麥當勞買一送一!10 塊麥克雞塊、薯餅、焦糖奶茶通通有 歡樂送買一送一、深夜食堂享 79 折
- 《寧安如夢》張凌赫擠走緋聞女友白鹿成GUCCI大使 新劇與徐若晗花瓣雨下熱吻甜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