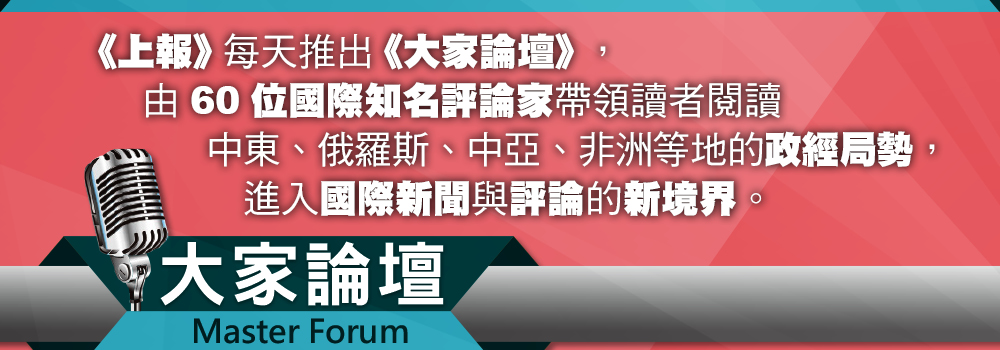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檢方第9度提訊!被問不法所得是否上億 柯文哲未回應 2024-12-11 22:35
- 最新消息 【大法官人事案】難忘被害人家屬絕望神情 王碧芳:我支持死刑 2024-12-11 22:16
- 最新消息 法總理上任僅3個月垮台 馬克宏擬48小時內提新人選 2024-12-11 21:56
- 最新消息 動輒飆罵下屬「混蛋」 數發部2主管涉霸凌降調非主管職務 2024-12-11 21:51
- 最新消息 南韓總統辦公室僅提交小部分資料 警方搜查行動無功而返 2024-12-11 21:28
- 最新消息 陸委會「有條件」放行雙城論壇 北市府:秉持4原則持續交流 2024-12-11 21:14
- 最新消息 【大法官人事案】反對翁曉玲版《憲訴法》 王碧芳:會癱瘓憲法法庭 2024-12-11 20:45
- 最新消息 保護本土產業鏈 美將宣布中國太陽能板關稅提高2倍 2024-12-11 20:41
- 最新消息 「一隻阿圓」穩交陳百祥 眼尖網友:去年就曾一起去韓國! 2024-12-11 20:10
- 最新消息 「入冬最強冷氣團」來襲周末恐剩10°C 中醫推薦「2種養身飲」暖身又暖心 2024-12-11 19:42


迪旺
●哈佛大學貝爾弗中心中東計劃教授
●巴黎科學與文學聯大阿拉伯世界研究院主席
新一輪暴動正在動搖阿拉伯世界,黎巴嫩和伊拉克剛剛加入了蘇丹和阿爾及利亞的行列。各國最近的群眾示威動員了社會各界的數百萬人,他們憤怒於經濟條件的惡化,認為管理不善和拙劣的治理加劇了這一問題。
和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一樣,各國目前的示威圍繞「政權更迭( regime change)」。
但有一個關鍵區別:先前的暴動是因為人們渴望尊嚴,而現今的示威是因為人們饑餓。
阿拉伯之春讓位給了不滿的嚴冬(winter of discontent)。
回到2011年,石油價格處於高點,許多阿拉伯經濟體增長速度為幾十年之最,暴動領導人主要渴望獲得更好的工作、發出更多的政治和社會聲音的年輕人,地區內許多政府能夠用擴展經濟政策平息街頭示威,資金來自石油收入、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的支持以及外匯。
但隨著2014年油價崩盤,這一財政空間也消失不見。
地區內十國政府債務-GDP之比已達75%以上,隨著增長放緩,公共支出也隨之下降,加劇了經濟不安全,即使在財政調整勉強起步的國家,租金分配的舊模式也已難以為繼,群眾對於無力、不願拿出令人信服的改革方針的體制怒目相向。
此外,阿爾及利亞、蘇丹、黎巴嫩和伊拉克的群眾運動吸取了2011年暴動的重要教訓。示威者不再滿足於推翻年邁的獨裁者,也把目標對準了國家、安全部隊,在阿爾及利亞、蘇丹,領導者拒絕迅速進行選舉,要求時間組織新政黨,從而與老牌伊斯蘭主義組織競爭。
除了要求政治制度的徹底變化,當前的示威者也拒絕與舊體制談判。
在阿爾及利亞,700億美元外匯儲備和微不足道的外國債務意味著示威運動和武裝力量能夠將目前的膽小鬼遊戲(game of chicken)繼續玩下去,前者在等待體制分崩離析,後者在等待群眾自行散去。
當然,風險在於在財政緩衝耗盡前無法形成解決辦法,導致經濟改革更加難以實施。
相反的,蘇丹民主陣線8月不得不與軍方達成了權力分享協議。
經濟的崩潰使得合作成為更合理的戰略,軍方不再能夠花費60%的國家開支(現已降至GDP的8%),目前,技術官僚政府正在負責穩定經濟,最終的政治討價還價被擱置,雙方都在角力,盼能從最終的轉型中獲益。
從這個角度講,黎巴嫩和伊拉克仍更接近阿爾及利亞而非蘇丹,但它們的經濟正在迅速惡化。
伊拉克受制於石油收入減少,黎巴嫩因資本減少而不安,資本流入是黎巴嫩主要的外部租金來源,這些經濟衝擊暴露了各國基於宗派政治制度的巨大成本,受經濟仇恨驅使的示威者因為整體安全環境改善,變得更加大膽。
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IS)的滅 亡以及敘利亞戰爭的減緩改善了整體安全環境。
在前述四國中,經濟管理不善的嚴重程度反映了國家支出被長期中飽體制盟友、和被保護人之私囊,沒有惠及全體人民,體制被各國私人部門透過裙帶主義(cronyism)所把持,不但攫取租金向被保護人輸送,還阻止可能為反對運動提供資金的自治實體的出現。
結果,資本和技能錯置,營商環境惡化,競爭、創新和增長都受到影響。
伊拉克和黎巴嫩的狀況因為各自人口的多樣性而進一步複雜化。
20世紀90年代黎巴嫩內戰後的政府、21世紀初美國入侵伊拉克戰爭後上臺的體制,都依靠與宗派寡頭間的權力分享維持,後者更透過鎮壓和恩澤維持地位,只要有足夠的好處能夠分給各方各自的被保護人,執政聯盟就可維持下去。
但當租金減少時,各方無法就如何分配損失達成一致,反而為了剩餘資源鬥個你死我活,導致經濟危機。
在黎巴嫩,這一鬧劇的成本主要由已脆弱不堪的金融行業承擔,隨時可能崩盤。
最後,區域地緣政治動態也影響著黎巴嫩和伊拉克國內政局,兩國受伊朗支持的政治集團擁有軍權,但到目前為止,兩者沒有能力都達成廣泛接受的社會契約,鞏固政治地位。
無論如何,阿爾及利亞、蘇丹、黎巴嫩和伊拉克都在創造歷史。
2014年以來,整個中東地區的石油收入暴跌了約1/3,獨裁體制用來維持恩澤的資源數量告急,時序進入2020年冬季,新一波民眾不滿可能爆發,吞噬其他國家,各國面臨的挑戰是找出一條政治、經濟轉型之路,既能滿足街頭,也能為廣泛共用的繁榮創造條件。
但到目前為止,面臨要求更公平、生產率更高的社會契約的群眾運動,老化的體制正訴諸於赤裸裸的鎮壓,這只能讓群眾敢於要求更多讓步。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們只能猜測。
目前尚無阿拉伯國家找到了可靠的前進道路,哪怕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起點:民主化的突尼西亞亦如是。
(原標題為《The Arab Winter of Discontent》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