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阿塞德軍隊為何潰不成軍 23歲士兵坦承:我把手機轉「飛航模式」棄槍逃跑 2024-12-13 11:31
- 最新消息 《蜀錦人家》譚松韻激吻鄭業成甜翻播放量破2億 他被抓包「親到滿臉漲紅」全網笑翻 2024-12-13 11:30
- 最新消息 行政院「霸凌通報平台」今天上線 3天內回報、1個月內要結案 2024-12-13 11:21
- 最新消息 避談是否舉行軍演 中國國防部發言人重彈「打獨不手軟」老調 2024-12-13 11:05
- 最新消息 高雄女騎士遇「野狗竄車道」慘摔車 再遭後方機車撞上送醫不治 2024-12-13 11:03
- 最新消息 飯店 buffet 日式主題登場!台北喜來登十二廚「北海道美食祭」升級不加價、台北凱撒 Checkers「日本美食盛宴」吃到飽 781 元起 2024-12-13 11:00
- 最新消息 嚴德發視導花東榮院為AI管理中心揭牌 讓偏鄉醫療智慧化 2024-12-13 10:57
- 最新消息 Capcom 宣布 2026 年推出《鬼武者》系列新作《鬼武者 Way of the Sword》 2024-12-13 10:38
- 最新消息 【雙城論壇】上海台辦主任、9中媒記者遭陸委會封殺 蔣萬安:很遺憾 2024-12-13 10:36
- 最新消息 科技巨擘加緊修復關係 WSJ:亞馬遜擬捐100萬美元給川普就職基金 2024-12-13 10:28

艾塞莫魯
•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
曾幾何時,美國政治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社會主義者永遠不能擔任高級公職。但現在成為美國民主黨總統提名主要候選人的卻是一位自封的「民主社會主義者(democratic socialist)」:美國聯邦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
美國是否應當接受這一變革?
民主黨人的初選內容比僅僅針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要多得多,人們渴望徹底解決嚴重的結構性經濟問題促成了桑德斯的崛起,在二次大戰後的數十年中,美國經濟生產率穩定成長,所有工人的工資(不考慮教育因素)平均每年以超過2%的速度遞增。
但這在今日已難以為繼。
過去40多年來,生產率成長乏善可陳,經濟成長放緩,越來越多的收益比例流向了資本所有者、以及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此外,平均工資停滯不前(透過通膨調整後),擁有高中學歷(或以下)的工人工資實際呈下降之勢。
只有少數幾家公司(及其所有者)主宰整個經濟,收入最高的0.1%拿走了國民收入的逾11%,此一數字在20世紀70年代僅為2.5%。
但民主社會主義是否能治癒這些頑疾?
作為一種視市場經濟為本質不公平、不平等且不可救藥的意識形態,解決辦法是切斷這種制度最重要的生命線:那就是對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相較公司及所有機械設備由一小群所有者掌握的制度,民主社會主義者更樂於接受「經濟民主(economic democracy)」,也就是將企業交由工人或由國家運營的行政機構所控制。
民主社會主義者將他們所設想的制度與蘇聯式制度進行對比,他們認為,民主手段完全可以實現目的。
但(拉美)最新的生產社會化嘗試嚴重依賴反民主制度,這恰恰引出了美國目前辯論的另外一個問題:民主社會主義已與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混合在一起,同時不幸的是,桑德斯助長了這種混亂局勢。
「社會民主」指的是20世紀整個歐洲,尤其是北歐國家興起並在歐洲佔據主導地位的政策架構,同樣側重控制過度的市場經濟,減輕不平等,改善最不幸群體的生活水準。
儘管桑德斯這樣的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往往以北歐社會民主為榜樣,但這兩種制度間實際存在著深刻必然的差異。
簡言之,歐洲社會民主的目的是規範市場經濟,不是取而代之。
我們以很早就與馬克思主義(Marxist ideology)意識形態和共產黨保持距離的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 SAP)為例,來瞭解社會民主政治的演變方式。
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的創黨領袖布蘭汀(Hjalmar Branting)創建了一個平臺,不僅吸引了產業工人,也吸引中產階級。
最重要的是,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通過民主手段爭取權力,在體制內為改善絕大多數瑞典人的生活條件而付出努力。在大蕭條後的首次選舉中,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領袖漢森(Per Albin Hansson)稱該黨為「人民之家(people’s home)」,並且提出了包容性議程。
選民們以高得驚人的41.7%的得票率獎勵了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使之與農業黨(Agrarian Party)結成了執政聯盟。
在又一次取得壓倒性選舉勝利後,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於1938年組織了一次由企業、工會、農民和政府代表組成的會議,此次會議在度假勝地薩爾斯巴登(Saltsjöbaden)開啟了合作勞動關係時代,決定了瑞典往後數十年來的經濟。
瑞典社會民主契約的關鍵支柱是集中設定工資制(centralized wage setting)。
按照雷恩-麥德納模式(Rehn-Meidner model,以2名瑞典現代經濟學家的名字命名),工會和商業協會談判了全行業工資,政府則負責維持積極的勞動力市場和社會福利政策,同時還投資於勞動者培訓和公共教育。
結果導致工資大幅縮水:所有從事相同工作的人,無論技術水準、公司盈利能力,均獲得同等數額的工資。
上述制度並沒有導致生產資料社會化,反而支援了市場經濟,因為它允許生產性企業繁榮發展,投資和擴張,競爭力較弱的對手卻為此付出了代價,因為工資水準按行業設定,由此產生的回報(利潤)得以留在生產率提高的公司。
不出所料的是,在上述制度下,瑞典生產率穩定成長,瑞典公司在出口市場上擁有極強的競爭力,此外,其他北歐國家也建立了類似的制度:在部分頗具說服力的案例中,建立上述制度的並非社會主義者或社會民主人士,而是中右翼政府(center-right governments)。
從廣義的角度看,社會民主成為戰後工業世界繁榮的基礎。其中同樣包括美國,新政(New Deal)和隨之而來的改革強化、建立了社會民主契約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集體談判、社會福利政策和公共教育。
當知識和政治潮流偏離以市場為基礎的社會民主契約時,情況通常就不會太好。
20世紀60年代起,瑞典和丹麥工會在更為激進的左翼力量影響下,全面擁護民主社會主義,並開始要求經濟民主和直接控制利潤。
在瑞典,引發了與企業的激烈談判,並因此設立了「工薪者基金(wage earner funds)」,於是公司利潤的一部分(通常以新股發行的形式)會被放入公司一級的勞動者基金。
上述變動破壞了企業和工會之間的合作協定,並扭曲了先前推動投資和生產率成長的激勵措施,截至20世紀90年代初,上述制度的缺陷已顯而易見,這套制度也因此而遭到唾棄。
當自由市場思想潮流導致社會民主契約右偏,同樣會帶來糟糕的結果。在生產率表現同樣溫和的情況下,不平等現象逐步擴大,只留下已然千瘡百孔的社會安全網路。
因此,我們需要的不是市場基本教義(market fundamentalism)或民主社會主義,而是社會民主。
美國需要有效監管來控制集中的市場力量,工人需要更大的發言權,公共服務和安全網路則需要加強,最後,但同等重要的是,美國需要一項新的技術政策,以確保經濟發展軌跡保障所有人的利益。
上述這些均無法透過公司社會化來實現,尤其值此全球化和技術領導型企業主導經濟成長之際。
市場必須受到監管,而不是遭到廢棄。
(原標題為《Social Democracy Beats Democratic Socialism》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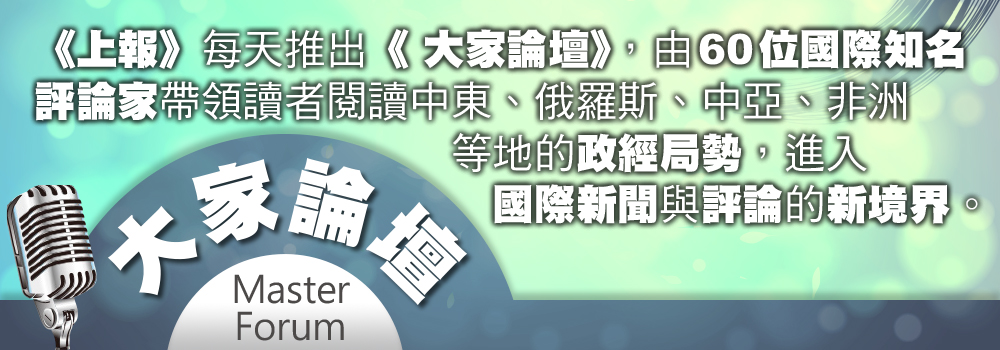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趙麗穎與《玫瑰的故事》林更新爆熱戀 她帶兒子看煙火他「這穿搭」現身放閃
- 趙麗穎與《玫瑰的故事》林更新被抓包穿情侶裝 兩人隔空示愛3證據曝光全網沸騰
- 張若昀《慶餘年》第二季流量奪冠成劇王 他開2千萬跑車因「這舉動」形象全毀
- 【有片】中華隊球員「無敵星星」吊飾哪裡買?博客來明日早上再次開放預購
- 《長相思》檀健次開唱勁歌熱舞嗨翻 卻被抓包在台上做「這件事」超噁心掀罵聲
- 《永夜星河》虞書欣新劇停拍3天劇組全換人 官方海報獨厚她卻沒男主角內幕曝光
- 譚松韻《蜀錦人家》與鄭業成吻戲被刪光掀眾怒 2敗筆熱度慘輸孟子義新劇《九重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