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國家層次」衝突結束? 情報人士:伊朗無意回應以色列攻擊 2024-04-19 21:02
- 最新消息 【強化制海資通】透過AI接戰系統整合 讓以岸制海打擊戰力發揮極大化 2024-04-19 21:00
- 最新消息 【強化制海資通】美售台新型野戰資訊通信系統延宕2年 重招商由L3Harris得標 2024-04-19 21:00
- 最新消息 黃子佼持7部少女不雅片案 高檢署發回北檢續查 2024-04-19 20:44
- 最新消息 「國際金卡納大獎」凱道賽車甩尾對決 19到22日交管一次看 2024-04-19 20:33
- 最新消息 把握好天氣 下周二鋒面接力來襲雨連下6天 2024-04-19 20:16
- 最新消息 竹縣、台東各一議員 6月1日舉行補選 2024-04-19 20:00
- 最新消息 北流1.9億追加案監察院糾正 蔣萬安:一上任積極處理 2024-04-19 19:47
- 最新消息 中國外交官駐外薪給罕見調漲 每月多領3.3萬元 2024-04-19 19:35
- 最新消息 性侵4童營隊狼師遭爆僅登記工作室成漏洞 議員憂:恐捲土重來 2024-04-19 19:26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進入相對穩定的年代,由謹慎小心與某種責任感所引導。這就是負責年代,但這個年代已然遠去。(二戰經典照片「勝利之吻」(The Kiss)/維基百科)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進入相對穩定的年代,由謹慎小心與某種責任感所引導。這就是負責年代。在很深刻的層面上,形塑這個年代的是選民和他們選出的代表所曾經歷的恐怖個人經驗。在他們面前的是滿目瘡痍而大火焚燒過的世界,是驚魂未定的全球人類。他們看到種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復仇心態、經濟衰退、貿易戰與深陷意識形態極端主義的駭人後果,因此一概予以摒棄。戰後,人類文明曾短暫滿盈樂觀主義,彷彿久旱後的甘霖。美國小羅斯福總統早在戰爭結束前兩年的1943年就描述了這種感覺:「我們有信心,未來世代將知道在二十世紀中期曾有一段時間,善意之士找到方法團結起來,共同生產,為了消滅導致無知、偏狹、奴役和戰爭的勢力而戰鬥。」
他形容的目標很單純,也達成了。蘇聯、美國、中國、英國與法國一致認同那是一場正義的戰爭,也了解他們見證到的恐怖意義重大。但共識僅止於此。羅斯福提到未來世代,但是他的世代見證了廣島與長崎的原子彈爆炸,不久又因蘇聯在1949年的首度核試爆而為之駭然。新的世界誕生了,卻面對滅絕的可能。
瑟瑟發抖的世界最大的恐懼是另一場世界大戰即將發生,起因是危險的冷戰敵對狀態。樂觀主義很快被深刻的悲觀壓過。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美國人以為蘇聯會與之合作達成世界和平,短短一年後,已經很少美國人認為蘇聯值得信任,而65%的美國人預測四分之一世紀內會再有一次全球戰爭。同時,根據一項民調,每十個美國人就有六個人希望聯合國更強大,甚至希望有單一的世界政府。
焦慮和恐懼有時也有好處,特別對統治者而言。好處之一是可以迫使人謹慎,而謹慎又帶來責任感。
負責年代可說是蓋洛普民調的編輯威廉.A.萊德蓋(William A. Lydgate)在1947年所定義的,那年他寫了一篇很長的調查分析:「在莫斯科丟幾顆原子彈這種極端做法對人民沒有吸引力⋯⋯然而,情勢看似如此黯淡可能是好跡象。與其像許多人在1918年之後那樣,理想化的以為世界環境對民主很安全,今天的美國人清醒的知道,和平必須靠努力維持。」
懷舊情緒不僅危險,也會騙人。冷戰感覺起來並不像負責年代。西方國家不情不願而往往經過暴力衝突才放棄了在開發中世界的殖民地。世界在古巴飛彈危機、柏林緊張情勢,以及韓戰和越戰中都聽到戰鼓隆隆。兩大強權透過一系列代理人戰爭相鬥,所謂第三世界的人民被犧牲在防止東西方發生核戰的祭壇上。
然而,那還是一個負責任的世界,即使是在事後認知到這一點,對於現在也有幫助。要辨識出現狀中的良善很困難,而要追蹤邪惡快速崛起的軌跡更難。戰後,世界領袖活在對一場真正具毀滅性的新衝突持續的憂慮中。多數情況下,讓他們自我克制,不走上軍事冒險主義一途的,正是他們的焦慮。民意更限制了他們,在蘇聯的宣傳言論與美國將軍的發言中,和平都是最高價值,至少領導者希望國民相信他們追求的是和平。即使是好戰的麥克阿瑟將軍都三句不離和平,他說:「士兵祈禱的莫過於和平,」也談及有必要「維護我們透過戰爭贏得的和平,」甚至說過應該為了和平而犧牲榮譽。
讓領導者受到責任感克制或限制的是意識形態嗎?不盡然。限制他們的是一股更深刻的力量,是對戰爭之恐怖的個人與集體記憶,以及他們從中學到的道德教訓。「一切戰爭始於愚昧,」甘迺迪總統在1961年柏林危機時說過。古巴飛彈危機時,軍方領袖向甘迺迪呈報將摧毀整個蘇聯集團的先發核子攻擊計畫(光在莫斯科就會投下170顆原子彈與氫彈),甘迺迪駭然離開了房間。「我們還自稱為人類,」他在走去橢圓形辦公室途中憤慨的對國務卿迪恩.魯斯克(Dean Rusk)說。
那個世界的領袖,例如赫魯雪夫與甘迺迪,以及南斯拉夫的約瑟普.布洛茲.狄托(Josip Broz Tito)、西德的康拉德.艾德諾(Konrad Adenauer)、以色列的大衛.本-古里昂(David Ben-Gurion)、英國的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蘇聯的里歐涅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和法國的法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都活過了一次或甚至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他們不是天真的和平主義者。反之,他們都有符合各自國家利益的務實目標,亦即穩定、國際機構、避免下一次大戰。
在西方,責任也以其他形式展現,如左右陣營極端勢力的衰退,以及對民主日益增長的支持。政治學者羅伯托.S.佛亞(Roberto S. Foa)與亞夏.芒克(Yascha Mounk)指出,1930年代出生的美國人中,超過70%的人認為生活在民主體制中對他們是「絕對必須」。
那個年代出生的英國人中,有此感受的人數幾乎一樣多(65%)。民主價值對於1940和1950年代出生的人同樣不可或缺。打造西方世界的人有一個改變生命的共同慘痛經驗──戰爭的可怕破壞。當前青壯世代的父祖輩有著跨越國界的共同價值觀。他們展現出近乎虔誠的勤懇正直,視當下為神聖的,不會抱持對未來的幻想。他們要求的是多少不偏離主流而負責任的政治作為,也得其所願。
負責年代緩慢而艱辛的帶來了相對穩定與和平。兩大強權間的對立競爭關係基本上仍是理性而負責任的。他們對民粹主義敬而遠之,專注在科學與技術發展以贏得冷戰,並改善社會的物質條件。在各自的勢力範圍中,兩大強權在他們所屬的國家集團中高舉國際合作價值。
誠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除了共產主義垮台後短暫的衝突激增,國家間戰爭減少了。最後一次有完整的裝甲軍團彼此戰鬥,是在2003年的第二次波灣戰爭。全球各地的衝突死亡人數急劇下降,每日生活費不到2美元的全球人口也是。兒童死亡率減少。1950年,全世界能識字寫字的人口不到一半,今天,這個數字是86%。2003~2013年間,全球人均收入中位數幾乎倍增。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發生。戰後時期傷痕累累的社會與憂心忡忡的領袖種下了一棵穩定之樹。這一切正是那棵樹的果實。
關於負責年代有兩件事情是必須知道的。
首先,在動盪不安與戰爭頻仍的現代,負責年代是個異數。第二次世界大戰讓極端主義和民粹主義噤了聲。雖然這段沉默在歷史上只是一瞬,但這本書多數讀者都是在這段時期誕生的。然後,對戰爭的記憶開始褪色。與1930年代誕生的世代不同,生於1980年代的英國人和美國人一般而言並不認為民主不可或缺。只有30%的人這樣想。他們的祖父也許在諾曼第海灘上為捍衛民主犧牲了生命,但他們自己卻多少認為民主只是沒有意義的詞語。
關於負責年代你需要知道的第二件事,你已經察覺到了:這個年代已然逝去。
負責年代隨著世貿大樓雙塔倒下而結束。我們活在911事件的最初餘波中。蓋達組織在美國國土的攻擊,是基本教義派對美國代表的普世主義願景發動的戰爭行為。恐怖份子企圖引發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全球戰爭,在此過程中他們釋放了先前被抑制的陰暗力量,其中許多與這兩大信仰毫無關係。這開啟了決定世界命運的戰爭,交戰方並不是宗教,而是觀念。一方相信世界正緩慢朝政治與文化融合前進,另一方認為這樣的未來是個噩夢,為了確保這樣的未來永不成真而甘願戰鬥。夾在中間的是全球的中產階級,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中產階級,在民族國家與全球化、特定身份與普世價值之間不確定的擺盪。
今天的全球化不可能永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相對和平受到威脅,而不穩定的跡象快速增加。其中最嚴重的是氣候危機,工業時代的繁榮,是以現在和未來的自然世界受到破壞為代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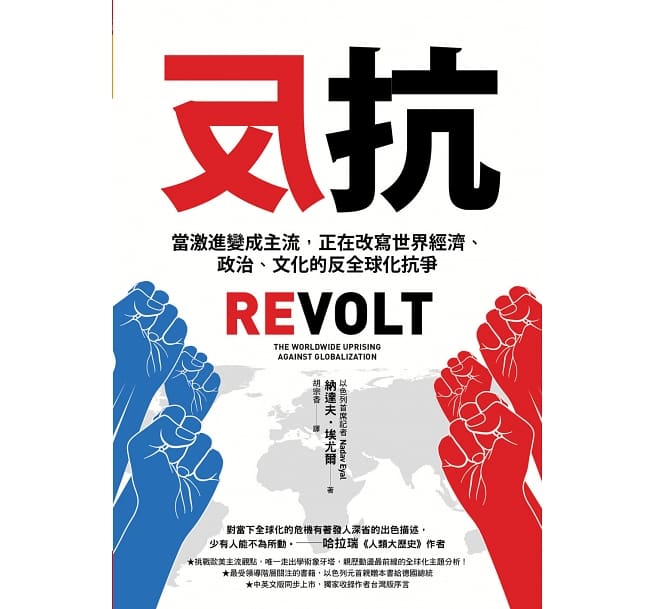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淚之女王》金智媛、金秀賢互飆演技收視破20% 「洪海仁墓碑」劇照瘋傳網憂BE結局
- 《蓮花樓》成毅新劇高馬尾造型曝光帥翻 憑2關鍵奪回藝名聲勢輾壓師兄任嘉倫
- 【《承歡記》內幕曝光】楊紫片酬拿2億演技卻被罵翻 許凱演霸總9千萬輕鬆入袋
- 《與鳳行》林更新公開女友惹怒CP粉 趙麗穎親上火線17字幫忙救場超暖心
- 《慶餘年》第二季5月播出全網沸騰 「他」接演肖戰角色2關鍵被看衰
- 【韓星片酬大公開】金秀賢拍《淚之女王》因「這理由」降價演出 IU身價輾壓宋慧喬
- 肖戰新劇凝視《惜花芷》張婧儀畫面曝光甜出汁 新片與《在暴雪時分》趙今麥演兄妹超吸睛
- 白敬亭拍趙露思《偷偷藏不住》姐妹作制服照曝光 「這關鍵」帥度不敵陳哲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