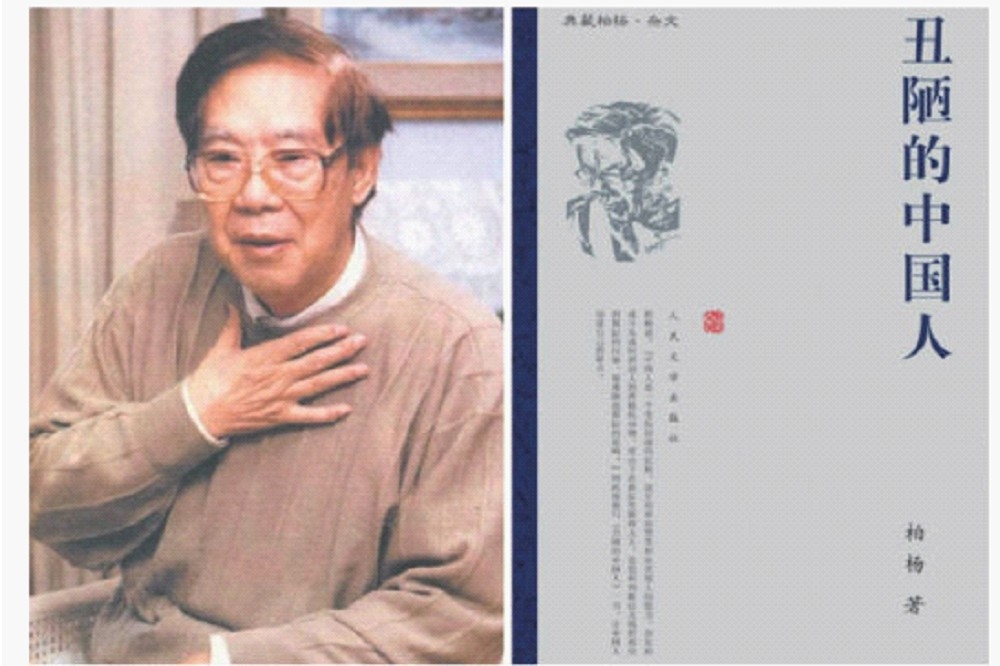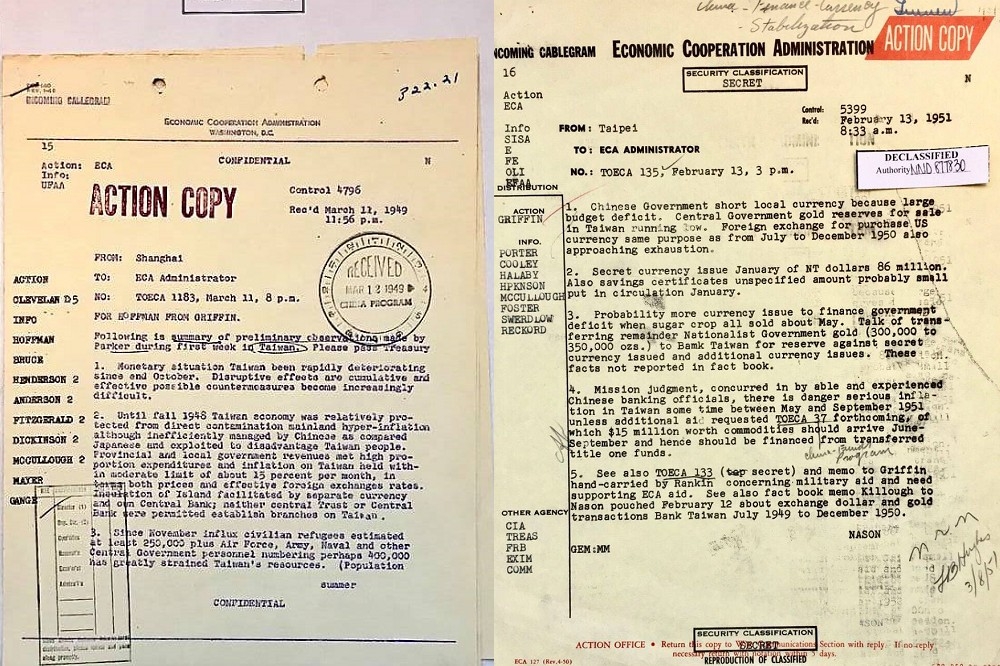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Toyz販毒關定了 秀30張公益感謝狀打悔過牌仍判4年2月 2024-04-27 12:54
- 最新消息 檢測報告造假逾30年! 日本老牌藥品「正露丸」遭勒令暫時停產 2024-04-27 12:46
- 最新消息 七寶媽三度道歉止不住火 13家廠商切割她急關粉專遭諷「又去避風頭」 2024-04-27 12:18
- 最新消息 《春色寄情人》李現擔任遺體修復師原因太揪心 他「隱忍式哭戲」封神全網讚嘆 2024-04-27 12:18
- 最新消息 發現二戰時期未爆彈 德甲美茵茲隊主場暫時關閉 2024-04-27 12:04
- 最新消息 金智媛《淚之女王》演活傲嬌千金「洪海仁」爆紅 她取代IU、朴恩斌奪女主內幕曝光 2024-04-27 12:00
- 最新消息 離譜!高鐵列車長酒駕值勤 檢舉人:已非首次規避酒測 2024-04-27 11:43
- 最新消息 結束3天訪中行程後 布林肯稱「已發現中國試圖操弄美國大選證據」 2024-04-27 11:10
- 最新消息 台灣地震頻率「衝破天際線」 氣象署估餘震持續3至6個月 2024-04-27 11:10
- 最新消息 7-11 思樂冰、咖啡買一送一!金色三麥「蜂蜜泡泡風味思樂冰」新口味登場 加碼推 4 款聯名鮮食 2024-04-27 11:00

江之翠劇場《行過洛津》劇照。(圖片摘自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本文旨於追溯台灣南管戲曲從1980年代以來的轉變。理論上,1987年解嚴以來,台灣主體意識提昇會有新一波的台灣文藝復興運動。南管作為台灣在地戲曲,應日趨繁盛才是。不過,隨著台語日趨式微,南管戲曲恐怕是日漸萎縮,從地方館閣消退到必須靠國家力量保護,在政府單位或藝術學院贊助與保存下,才得以不絕如縷。
蔡小月旋風
國民黨據台以來,在黨國機器宣揚下,台灣文化往往被貶抑。如台語、檳榔、機車、拼裝車、原住民文化、廟會、歌仔戲與布袋戲等等,都被視為不入大雅之堂。傳承千百年的大眾文化如斯。那麼流傳在鄉紳之間的雅文化,如南管戲曲,就更是岌岌可危了。
為了突破黨國機器的包圍。台灣文化往往得透過西方強勢文化的認可,然後再回流到台灣來。如原住民歌曲在台灣本不登大雅之堂,可是自從飲酒歌,在巴塞隆納奧運會被選為開幕曲以來,蔚為流行。電影賽德克巴萊幾乎整片配樂都採取原住民傳統曲調。與原住民曲調流行類似,南管音樂也因蔡小月( 南聲社 )在法國演出、廣播,造成轟動。讓國人意識到台灣自有典雅的室內樂,如泣如訴的靈魂詠嘆調。
1982年,蔡小月在法國所造成的轟動,許常惠如此報導 :
南聲社的藝術家於十月十六日到達巴黎,於十一月九日離開巴黎。這二十四天,他們從沒有停止練習,可見他們的責任感重。儘管新環境不適應、旅途疲勞、語言溝通困難,但他們沒有一刻放棄努力,以期演奏會的成功。結果他們的情緒高昂,使他們在藝術的表現上達到最佳水準。三個星期裏,跑了五個不同國家,舉行十二場音樂會,這就是南聲社所達成值得驕傲的工作。
十二場音樂會,沒有一次例外,每場聽眾都是爆滿的,經常使我們不得不謝絕進不來的聽眾。從第一場在杜爾市演出,歐洲的聽眾便發現了南管音樂與南聲社音樂家所具備的罕有而寶貴的藝術特質。聽眾愈來愈多,在杜爾市的首場音樂會,入場券是贈送的,來了四百聽眾告滿。在科隆賣票時,聽眾達一千人。至於那一場由法國國家電台轉播的音樂會,估計在法國及歐洲其他國家有三百萬人在收聽。
聽眾的反應告訴我們,最欣賞南管音樂的古老的真實性。這個真實性不僅因它的音樂本身,更包括南聲社的社會與宗教背景所造成的氣氛。他們對已往在歐洲表演的中國藝術或音樂,通常是經現代化、西洋化或官方化的形式表演,感到遺憾與惋惜。因為歐洲聽眾很難忍受不純的或混雜的藝術。
新聞界的反應極佳,而且一致稱讚南聲社的演奏。十月廿二日巴黎「開放日報」(Libération)說:「精緻的歌聲達到最柔和的境界,這種音響只能以中國古畫與古瓷器的美來形容。」「世界日報」(le Monde)說:「南管音樂保存了極豐富而珍貴的古典中國音樂形式,而它給我們聽到的真實感可以與歐洲中古時代的遊吟詩人相比,它所唱的詩包含人們的愛情、歡樂與痛苦。」
從這篇報導中,我們發現:一般人很難區分南管戲曲與所謂中國藝術或音樂的不同。迄今,還是很多人以為南管是國樂的一種。不過,法國人很快發現南音與現代化、西洋化或官方化的表演形式很不一樣。雖然他們還是以中國古董、古瓷器或古典音樂,來認知台灣南音。

其實,南音與國樂有很大的不同。台灣所謂的國樂是中國現代化以來,高度西化的樂種。他的樂譜是西方八分音符樂理寫成的。他所追求的合音也是Do Mi So,不同樂音,依黃金比例,高低交錯。他所使用的樂器更是為了表現張力,而高度西化,如在弦樂器上都使用鋼弦。打擊樂用繃緊的鼓皮製成。相對的,台灣南音樂譜還是採用X 工 六 士 一,五分音符。(宮商角徵羽)。其和音則是繞著主旋律,陰陽交錯而成。琵琶彈骨幹音。洞簫加入裝飾音。兩者都屬陽。然後,又加入約莫低八度的樂種:三弦若即若離,跟著琵琶走;二弦補洞蕭之不足。南音弦樂都採絲弦,有彈性的,可是表現力度較差的。打擊樂使用所謂的壓腳鼓,除了用手打擊之外,還要一面用腳壓鼓,調整鼓皮張力來表現。
南音戲曲,或稱梨園戲中的身段,也跟所謂國劇或崑曲有很大不同。就梨園戲看來,後兩者的身段都過於僵硬,恍若魁儡或機器人。梨園戲中每個演員在唱工、身段、唸白方面皆有一定規範,所謂「三步進,三步退,三步到台前」、「舉手到目眉,分手到肚臍,舉指到鼻尖,拱手到下頦」等成規。要求表演者的尺度嚴格:務必要求唱、唸與科步配合得宜,每個動作細節都要交待清楚,無聲不動、有歌必舞。
南管戲曲要求細膩,近乎龜毛。如南音洞簫尺度,不僅音要準,還得使用竹材,在特定長度範圍內,竹節符合十目九節的法度。有時找遍整個山頭,都找不到一根適合當洞簫的竹材。南音唱腔,每個字,每個音,字首、字腹與字尾,更是含混不得。琵琶、二弦與三弦,也都有各種嚴格尺度:如一定使用梧桐木、玳瑁角、蟒蛇皮與林投樹根等等。唱曲、演奏則一律得背譜,著腹,不準看譜,主唱與樂師皆然。
這些林林總總的文化尺度,當台語文化逐漸式微時,讓南管首先從鄉紳室內樂淡出,退到寺廟館閣裡。然後,在蔡小月旋風之後,還是欲振乏力,館閣凋零,又退卻到不得不靠政府體制的幫忙了。
今日學習南音門檻非常高,主要是語言本身就構成很大障礙。南音語言大體採泉州腔,少數潮州腔和明代官話。除此之外,又包括古韻與文讀。換言之,姑不論泉州腔與潮州腔的差異,每個字詞就有三種不同念法,文讀、白讀與古韻。如北這個字,北、腹與寶( 以一般台語來念) 都有可能。又如一,一、素與即,同樣有三種不同讀法。那何時採古韻,採文讀,採口白或用官話來唱,卻又沒有一定規則。一般就是看師承,口耳相傳。風打梨的風,就是不能念成風,而是要唱成古韻,荒。唱錯了,南音老師就是不能接受的。
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研究,進入2020年之後,以台語為母語的人幾乎就是零了。然後到2050年,等到老一輩說台語的消逝,台語就算滅亡了。目前台灣出生的小孩子,一開始接觸到的語言,已經很難是台語、客語或原住民語。在學校、銀行等公私立單位都很難碰到講台語的辦事人員。商店也是。除非到傳統菜市場去,阿公阿罵逛街的地方,才會聽到各種「方言」。年輕一輩單是口語的台語文都沒甚麼條件說好了,那更複雜的南音漢語要唱好,那就更沒譜了。
所以,現在十幾歲的年輕人要學南音,除非有家學淵源,否則一般都要到學院裡,靜下心來,重頭學起。這對南音傳承有很大的影響。
然後,現在音樂強調專精。南音卻剛好相反。學南管的人,要坐過每一把椅子。一般從唱曲拍板開始,然後彈琵琶,學洞簫;在進入三弦、二弦。最後又學到壓腳鼓等等,那就幾乎是整個樂器都熟悉,可以當先生了。入門門檻高,要熟悉不是自己母語的語音,然後要出師到當先生,又得整個樂團交椅都坐過。如此要成材,像蔡小月那樣,在十五、六歲,在唱曲功力就足以錄製唱片,讓國際驚艷。這傳統到了二十一世紀,幾乎可以說是一去不復返了。
承先啟後的艱難,可以看看現在館閣裡約莫都是五、六十歲以上的人,可見一斑。

許全義說,他的阿公在鄉裡,可以說鄉紳了。因為村裡唯一的碾米廠,就是他在看顧。米絞(碾米廠)在日本時代就是鄉里資本象徵的結晶。然後,家族裡還有薄荷油工廠。聽說他是一般唱著南管,一邊嚼檳榔時,過世的。他可以當先生,教導一個南音團。可是,等到許全義父執輩時,就幾乎是失傳了。只有單獨玩樂器的,如吹洞簫和拉二弦的,湊不成一個團了。
然後,到許全義那一輩,經過國民黨嚴格國語政策洗腦下,現在五十歲左右的人,在麥寮鄉,就很少人玩過南管,甚至連好好聆賞過都沒有。南管從鄉紳的日常生活脈絡中,退縮到以廟宇為據點的館閣內。而且只有少數地方的廟宇才有南管館閣,如北港、鹿港和府城等等。小地方、無此傳統的新興城市、小廟宇也都很難找到可以湊成一團純音樂的,更不用說無聲不動、有歌必舞的梨園戲曲了。
目前還有先生在教、也可維持成團的傳統梨園戲曲,或許只剩下大甲吳素霞老師指導的合和藝苑了。其他的可能就要在學院或政府贊助的體制,或是梨園戲是主是輔,妾身難明的表演藝術團體了。
江之翠的興起
就算蔡小月旋風吹回台灣,南音依舊凋零。這自然是有志之士所難以忍受的。江之翠的周逸昌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周逸昌留學法國( 1876-84 ),學習劇場。留法期間,他就扮演起黨外人士與島內外訊息傳遞者的角色,是一位在戒嚴時代甘冒身家性命的風險站在人權與歷史正義這邊的人。當年這種人其實是一股默默支持翻轉台灣社會的力量。回國後,他一方面玩劇團,企圖在其中找到屬於台灣人的身體,那種真正台式的精神。一方面也積極參與社會,如反核四、蘭嶼核廢,廢除國民大會、刑法100條101條、520事件(農民運動)等等。

他如此好動,又是留法、學劇場的。1982年的蔡小月旋風,自然引起他的注意。1988年尤清擔任台北縣長,任內尤以台灣文藝復興為己任。或許在尤清的幫忙下,1992年江之翠劇團成立。那是台灣罕見的,學院外,專任有給職的,全面復興梨園戲曲的劇團。後來知名的漢唐樂府、王心心南管樂團,成員一般都還要靠演出費過活。沒演出,沒收入。不像江之翠的團員,每個月固定有微薄薪金收入。
台灣梨園戲曲式微,劇場文化卻相當強勁。如何結合這兩者,一直是台灣南音創新發展的主旋律。在漢唐、王心心樂團中,南音大體是配樂,襯托現代劇場的肢體動作;或像個人演唱會來呈現。相對的,江之翠就很認真的復育梨園戲曲。2006年,江之翠的朱文走鬼一劇,獲得台新表演藝術獎,聲名鵲起。
此後,江之翠成為國際知名的劇團。他們的劇種,朱文走鬼與行過洛津( 陳三五娘 ),都曾在世界各大歌劇院演出過。讓大家知道,原來台灣傳統戲曲如此典雅與細緻;傳統台灣精神對愛情與自由的追尋,至死不渝。

有關朱文走鬼這齣劇,蔡孟凱評論說:
《朱文走鬼》由江之翠劇場和「友惠靜嶺與白桃房」共同製作,改編傳統梨園戲「上路」流派的同名傳統劇目,講述秀才朱文於客棧邂逅被養父母凌虐而死的少女鬼魂一粒金,朱文在一粒金欲拒還迎的挑逗之下與之相好,在一連串荒謬逗趣的風波之後,人鬼伴侶踏上旅途。《朱文走鬼》以梨園戲之文本、音樂、表演程式結合日本的能劇、舞踏元素和舞台美學,企圖藉由將「情愫織入現代性的身體與空間感」,進而「與當代產生連結」。
《朱文走鬼》的劇本內容和表演程式基本仍是在傳統梨園戲的範疇裡頭,只是舞台改作能劇舞台的「本舞台」和「橋掛」形式,並在演出的頭尾和過門處,添入能劇中的說書段落(由舞踏演員芦川羊子詮釋)。可以說,《朱文走鬼》的策略是把傳統梨園戲的《朱文走鬼》「近乎」不更動地放在能劇的脈絡裡,比起近年百家爭鳴的各種跨文化/跨領域創作,其跨界概念相對而言可以說十分簡單。
但簡單不代表無效。偏偏就是這幾個看似微小的新添螺絲,讓《朱文走鬼》在原本庶民歡樂的氛圍之下,硬是多了幾分衝突與辯證。無論高起的能劇舞台,和象徵連結俗世與幽冥的橋掛;抑或是開演前樂師、表演者持燈如鬼火於黑暗的舞台空間中列隊進場,皆在在提醒著觀眾自身與劇中時空的距離。芦川羊子猙獰、誇張的舞踏表情,和義正詞嚴、鏗鏘有力的說書語氣,則勾勒出與歡快的戲劇內容大相逕庭的奇幻詭譎。在客棧一幕結束,〈走鬼〉之前,芦川羊子一段約兩分鐘、沒有口白的表演,將整部《朱文走鬼》割開,是在諭示朱文的未來?批判戲中人的愚蠢?抑或是嘲諷少女幽魂的心機?觀眾大可以給出數百種解釋,但這一段短短的肢體表演無疑將觀眾從嬉鬧的情節中抽離,提供一個更具批判性、更為超然的觀看視角。
從此評論中,我們可以知道:閱聽大眾基本上還是將其定位為現代劇場演出,而非梨園戲曲。梨園戲的處境一如劇中女主角,一粒金的處境類似,死了才能獲得愛情與自由。讓大家忘了梨園戲曲,才能認識到台灣人的身體與台式精神,如此雅致與熱情。
學院內的梨園戲曲,在吳素霞老師的耕耘下,當有其發展。不過,目前網路上能看到的,只是單曲表演,如畫眉,比較是詩的表現形式,而非一齣戲,唱作俱佳地完成一個故事或小說。又如從下圖曲目看來,2020年12月合和藝苑的演出,就只是謹守蔡小月,南聲社的演出規模,指、曲、譜三段式的室內樂演奏。
學院內的孤芳自賞,有時不利於澄清社會大眾有關梨園戲曲的迷思。如我們在網路上泉州南管戲曲演出的影片,會覺得那是跟歌仔戲類似的劇種。實際上,無論音樂性、身段動作的表現,台灣梨園戲之道地與雅緻,絲毫不下於崑曲,更不用說國劇與歌仔戲了。
總之,從蔡小月到朱文走鬼,我們一方面看到有人試圖復育台灣傳統仕紳文化,南音戲曲,走上國際舞台。一方面我們也見證了,老成凋零,文藝復興維艱。其中最艱難的是一整個世代的台語文文化消逝。南管戲曲是棲身於台語文文化的劇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台語消亡,有一天南聲社、江之翠、漢唐與王心心都將隨之凋零。我們要聽南音,欣賞戲曲,或許只能在學院內或是博物館裡了。簡之,只用國語來親近華夏文化,讀詩經、唐詩無法押韻,讀朱子( 生於福建,死於福建 )七零八落,沒有方言文化,民間戲曲,那依舊不是屬於華人的文藝復興。
※許可風為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學生、許全義為台中一中教師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吳磊哭哭】趙露思與張藝興現身新疆爆熱戀 3大證據被抓包全網沸騰
- 麥當勞買一送一!10 塊麥克雞塊、薯餅、焦糖奶茶通通有 歡樂送買一送一、深夜食堂享 79 折
- 成毅新劇虐戀李一桐預告曝光400萬人爭睹 他白髮揮舞火劍帥度超越《蓮花樓》
- 大雨狂炸補水!曾文水庫降雨達18毫米 南化水庫7小時進帳逾4萬噸
- 白敬亭、章若楠演《偷偷藏不住》姐妹作 兩人甜摟畫面曝光3敗筆被嘲「情侶變父女」
- 肖戰新劇搭檔《惜花芷》張婧儀3大高甜名場面搶先看 兩人夜會甜蜜相擁CP感爆棚
- 楊紫《長相思》虐戀檀健次、鄧為掀淚海 第二季張晚意冷血復仇埋悲劇結局
- 《春色寄情人》李現、周雨彤CP感爆棚收視狂飆 兩人戲外被喊「在一起」竟都羞紅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