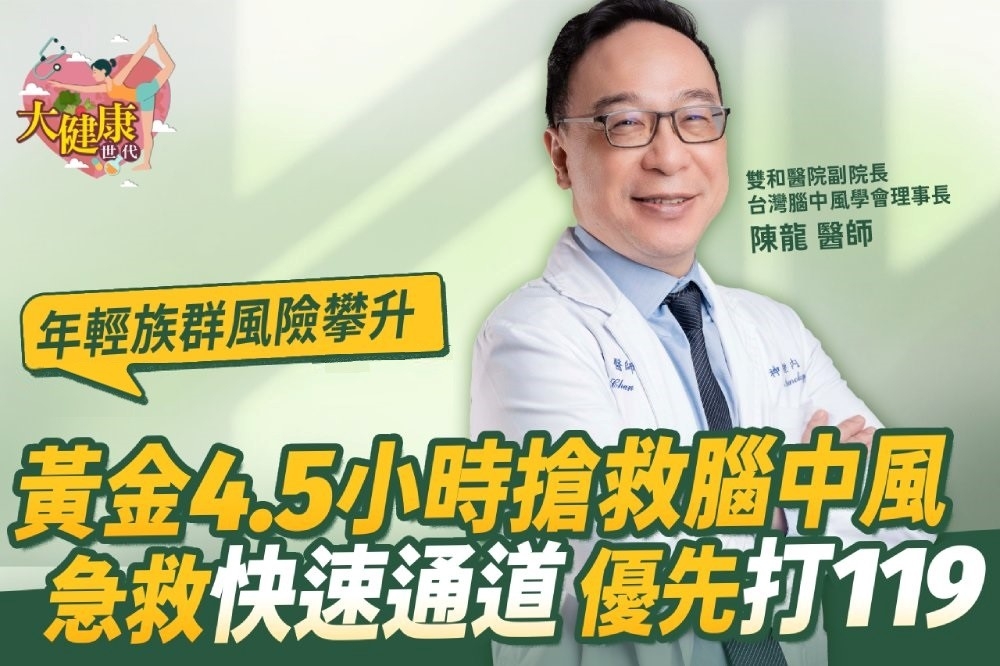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一沐日不只有草仔粿!再推「九層塔」台灣味 獨家「高讚塔奶蓋」手搖飲新登場 2025-05-28 07:00
- 最新消息 吳崑玉:無人機飽和攻擊的應對與進化 2025-05-28 06:00
- 最新消息 何清漣專欄:川普 vs.哈佛 美國文化戰爭中的堡壘戰 2025-05-28 06:00
- 最新消息 洪秀柱率團赴北京見王滬寧 名單驚見天王御用作詞人方文山 2025-05-27 22:50
- 最新消息 台大性騷爭議名醫請辭婦產科醫學會理事長 立委促衛福部釐清懲戒標準 2025-05-27 22:40
- 最新消息 藍委控刪地方補助款違法濫權 政院引《地制法》:酌予補助未違法 2025-05-27 22:33
- 最新消息 連署書剔除草簽遭質疑 南投選委會:比對姓名非比對簽名 2025-05-27 22:14
- 最新消息 川普對普丁不滿情緒升高 WSJ:白宮考慮本周對俄祭出新制裁 2025-05-27 22:01
- 最新消息 北院裁定柯文哲續押2個月 民眾黨3點怒批雙標、侵害人權 2025-05-27 22:01
- 最新消息 家寧男閨密是他!台灣首位公開出櫃男藝人 割席狠酸:我不吃鮑魚 2025-05-27 21:36

末期病患的免疫系統已難提供有效的自體免疫細胞。若能提早使用細胞治療方法,將可望使更多病人獲得有效救治。(美聯社)
想像一下,台灣病患以後可能面臨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情況。在台灣如果你是生命末期或嚴重失能,你無法請醫師結束你生命,因為尊嚴死沒有合法化。為避免將來的生命末期或嚴重失能,若既有療法無效時你也不能尋求細胞治療,因為法律不許。你只能等到末期和失能時,你才被「恩慈」地允許申請細胞治療,但實際上不會有醫院能幫你,因為曾經存在的細胞治療公司都倒閉了。
與國際趨勢背道而馳的細胞治療管制
近日,各界針對《再生醫療法》第九條之內容認為衛福部過度「放寬」再生醫療技術,應強力限制在「危及生命或嚴重失能時」始得申請再生醫療技術。如此限縮的管制架構在國際間非常罕見,亦不符合美國FDA人類細胞/組織相關產品(Human Cells, Tissues, and Cellular and Tissue-Based Products; HCT/P)規範之管制模式。細胞治療技術本就應針對其特性區分出風險高低而為不同之管制架構,以美國HCT/P為例,依據法規 21 CFR 1271.10(a)中之聲明,HCT/P只要符合四個條件,即視為一種「醫療技術」而非「產品」來審查,改由美國公共衛生服務法361款(Section 361 of 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 PHS361)管理。此四個條件分別為:
一、最小操作(Minimal Manipulation):針對結構組織,製程並未改變組織原有相關特性,例如組織之重建、修復或替代功能有關,以及細胞或非結構組織,相關製程並未改變細胞或非結構組織的相關生物特性。
二、同源使用(Homologous Use):捐贈者的細胞或組織物用來修護 (repair)、重建(reconstruction)、替代(replacement)或補充(supplementation)病患的細胞或組織物,而該細胞或組織物用在病患身上的基本功能(basic functions)與捐贈者(包含自體使用)相同。一般只要細胞或組織用於修護、重建、替代或補充多是屬於同源使用。
三、不合併其他物質使用(no combined with other articles):執行細胞治療時,未與其他藥品或醫材成分併用。
四、沒有系統性影響(no systemic effect):不會對病患的身體產生系統性作用。
美國FDA與歐盟EMA細胞治療均以產品管理方式為主,但也均設有風險較低的例外情況就以非產品列管,風險較高的細胞治療則以產品製劑管理,例如美國的PHS351細胞治療須申請試驗中新藥(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IND)跟生物製劑藥品上市查驗登記(Biologics License Application, BLA)),並進行相關臨床試驗已驗證其安全性與有效性。若真如反對者主張僅允許在末期與失能才能使用細胞治療技術,這與國際細胞治療管制趨勢完全「背道而馳」,是走回頭路迫使病患再次面對絕望。
幫大藥廠築起一道商業護城河
2015年由卡斯柏發起的連署,是台灣首見的right to try運動,其宗旨為:「台灣癌末病患至今無法享有這項治療方式,只是因為法令太過老舊,無法讓這項先進的治療在台灣合法進行,讓台灣的癌末病患喪失更多治療的選擇」,因此催生了細胞治療的發展。現在的反對者說,再生醫療法不可犧牲病人權益,但病人權益包括得到救治的機會,也就是「醫療選擇權」。當政府試圖進一步制度化時,卻面臨了以病人權益為名的反對,此種反對無疑是全盤否定了細胞治療技術發展空間,也再次抹滅病患之希望及「醫療選擇權」,致使病患將只能再次前往國外接受細胞治療!
若再生醫療法如同反對者訴求的限縮第九條,實際上就是幫大藥廠築起一道商業護城河,最終病患僅能選擇經過臨床試驗且天價的細胞製劑,如需要支付1200萬台幣的CAR-T細胞製劑!甚且目前台灣只有「B 細胞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的癌症兒童能接受CAR-T製劑治療,其他疾病目前「均無」相對應的「細胞製劑」可提供治療。如此情況下,不就是犧牲病患的「醫療選擇權」,要求病患僅能選擇「富人醫療」的細胞治療製劑,此舉無疑是謀取大藥廠「最大化利益」之行為,將為大藥廠奠定市場的壟斷地位。然而,細胞治療在本質上介於療法與產品之間,各國的管制就是在這兩端之間找平衡點。若以產品製劑管理細胞治療技術,因其須合乎cGMP的製程品質與環境監控規範,將會大幅度提升生產過程中的管控成本,更別說執行臨床試驗所耗費的大量人力、時間及金錢成本,增加的成本最終都還是轉嫁至病患身上,最後可能只會有昂貴的再生製劑,甚至迫使未來健保可能需負擔天價級細胞製劑,增加健保財政之困難或加速健保破產。台灣市場相較於歐美各國較小且進駐成本高,導致國際大廠沒興趣投入進而可能直接拋棄台灣市場,最後導致台灣病患無合法細胞治療產品可用。
究其實質,這場以病人權益為名的再生醫療法反對倡議,根本就是失焦的討論。行政院版本之《再生醫療法》第八及第九條其立意良善,既能提供病患的「醫療選擇權」,又能降低細胞治療相關成本,同時具備審查機制。《再生醫療法》第八條第一項:「醫療機構使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再生製劑或執行再生技術,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經核准後並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登記,始得為之」。亦即為確保病患接受再生醫療之品質、安全性及有效性,並採較嚴謹之管控機制,醫療機構使用再生製劑或執行再生技術時,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且應具備相當之資格與技術能力,方可獲准執行。
此外,第八條第三項亦明定主管機關應就再生製劑之指定、申請核准之條件與程序、核准效期與展延、廢止、核准事項變更、費用審查與收取、退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制定相關規範。再看《再生醫療法》第九條之條文說明則明確指出醫療機構在:(1)治療特殊病人之緊急需求;(2)經施行人體試驗已累積相當數據顯示初步成效;(3)已有其他實證文獻充分支持安全性及療效之細胞治療等三種情形下,可免依再生醫療製劑條例規定申請藥品許可證或有附款許可,但仍需回到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於執行前申請核准及辦理登記,且第一項第二款施行之人體試驗,針對其期別、條件會有所規範,而第一項第三款細胞治療項目也規定應有國內、外文獻作為實證基礎,確認其安全性、療效可預期,才可開放申請執行,亦即為目前特管辦法附表三及非附表三之管理機制。總觀行政院版《再生醫療法》第八及第九條相關規範架構與邏輯,並「不存在」如諸多學者專家所擔心醫療機構在違反科學依據與臨床倫理基礎下,可援引第九條「無限制」申請各種高風險細胞治療技術,更不是以第九條就能開個大門讓醫療院所自行濫用細胞治療技術來騙錢,這是胡亂斷章取義的理解。
提早使用細胞治療可救治更多病人
持平而論,行政院版本《再生醫療法》第八及第九條因其相關配套尚不明確,確實會引發各界擔憂。針對第八條第三項應說明再生醫療之品質、安全性、有效性及收費預期將如何制訂相關規範。再生醫療之品質可參考美國符合PHS361四項條件之細胞治療技術,以「聯邦規章典集第21章第1271部分(21 CFR 1271(HCT/Ps)」之「優良組織規範」(cGTP)或延續特管辦法之「優良組織操作規範」(GTP)進行管理。再生醫療之安全性、有效性及收費應讓收費審查機制能反映療效預期性。以臨床試驗的階段、數據、有效性及安全性等科學數據為基礎,建立療效與費用對應的審查機制。依據科學證據與風險高低評估病患、廠商及醫院三方各自應負擔之費用。舉例來說,缺乏足夠實證支持其安全性及初步有效性之再生醫療技術,廠商與醫院應負擔絕大部分費用,病患僅需承擔部分費用;具備安全性且已證實有療效之再生醫療技術,則可提高病患負擔之費用,並適時將療效良好之再生醫療技術納入健保部分負擔中,如此可以避免出現無療效卻要病患支付昂貴貴用之情形。而針對第九條則應於相關辦法中明訂再生醫療技術應用之範圍,其範圍可參考PHS361或特管辦法附表三之範疇,並嚴格規定執行再生醫療技術之捐贈者細胞來源是否應先限縮於自體細胞同源使用,待未來生物醫學發展趨勢明確證明進行異體細胞治療之安全性與初步療效,再滾動檢討修正相關辦法是否能開放異體細胞治療。
以上均是值得各界提出建議並詳細討論的議題,而非直接就將第九條的第二款與第三款刪除,將一切打回2018年特管辦法修訂之前的狀態,讓細胞治療在台灣瞬間斷絕生存空間。再生醫療是需要累積學、研、醫、產、藥等各界之執行經驗,以提升再生醫療技術成熟度與精準治療。現行特管辦法的一大限制就是規定實體癌第四期,標準治療無效才可施行免疫細胞治療,這是將其視為最後手段,卻也喪失了真正驗證其療效的機會,因為末期病患的免疫系統已難提供有效的自體免疫細胞。若能提早使用細胞治療方法,將可望使更多病人獲得有效救治,台大免疫學權威江伯倫醫師及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放射腫瘤科主任郭于誠均在「報導者」的專題中也如此主張。原本我們可期待再生醫療法之立法可突破此框架,但現在的討論卻是在走回頭路。
反對者甚至提出應以藥害救濟法來套用再生醫療法之主張,此種主張亦顯示對再生醫療技術缺乏認識。自體細胞且最小操作,在國外就不需要以產品管理,即便是CAR-T製劑,也是屬於應用自體細胞培養生產,其操作流程與個體差異性會導致製程有所差異,無法讓CAR-T如同傳統藥品之特性,具備製程的一致性與穩定性。再生醫療法上的再生技術既然不是產品模式,就不應適用《藥害救濟法》下的無過失責任補償,而是回到醫療法上的過失責任,頂多加上責任保險。若要說無過失責任補償才是保護病患權益,那等於是所有醫療責任都應改成無過失責任補償制才合理。此議題已討論多年,均已有共識再生醫療技術其性質並不適用於藥害救濟機制,因此於《再生醫療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醫療機構執行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之再生技術,發生不良反應致傷亡應有救濟保障措施,並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就該措施之方式、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進行規範。以台灣現況而言,多數使用免疫細胞療法的癌症病人,其實都合併使用其他正式核可的標靶或化療藥物。在合併用藥之下情況下,又該如何界定相關因果關係呢?這些似乎都不在相關主張者所考慮的範圍內。
※作者為臺北醫學大學新藥研發博士學位學程博士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2025 端午節】全台 12 家人氣冰粽推薦!星巴克、義美、85度C、元祖、紅豆食府都有 乖乖竟然也出粽子
- 【內幕】輕巡艦量產計劃縮水 減少5艘改2500噸雙船體火力艦
- 劉宇寧、宋祖兒《折腰》2大敗筆Netflix收視下滑 慘輸秦漢與謝盈萱新劇《忘了我記得》
- 《藏海傳》爆紅肖戰接演《知否》導演諜報新劇 搭檔《愛情而已》的「她」遭粉絲抵制
- 《折腰》宋祖兒主動吻上劉宇寧全網暴動 她躺床撒嬌喊「這句話」全網甜暈
- 楊冪新劇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趙又廷合作破局 改搭《難哄》的「他」被酸資源降級
- 《藏海傳》肖戰演技超越舊作《慶餘年》獲好評 劇情卻因2大敗筆慘遭吐槽
- 《藏海傳》肖戰、張婧儀船上調情「這段話」竟是即興演出 他戲外幫她整理頭髮互動超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