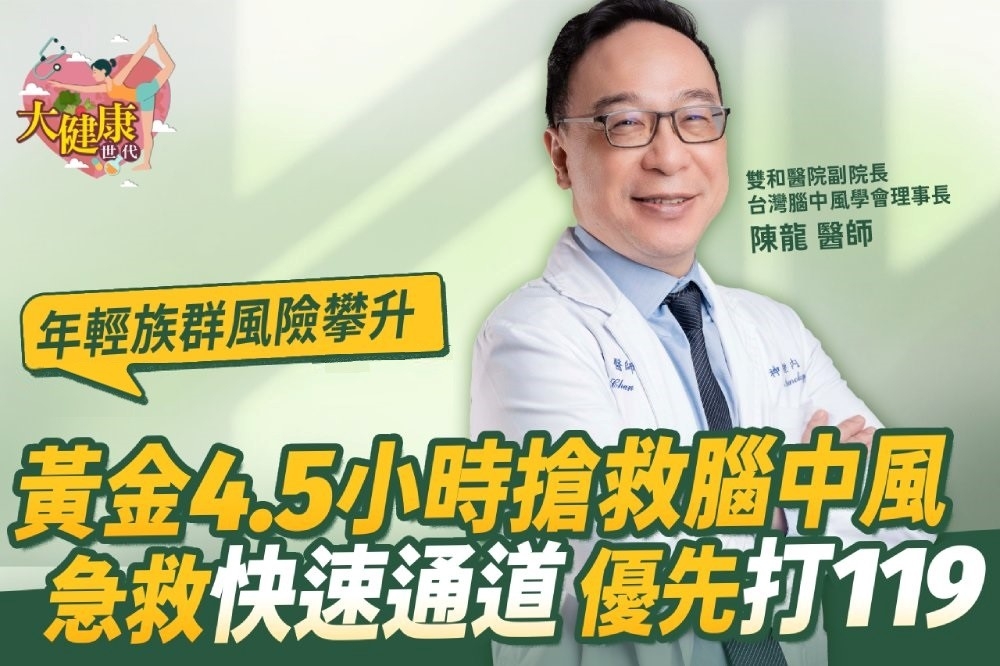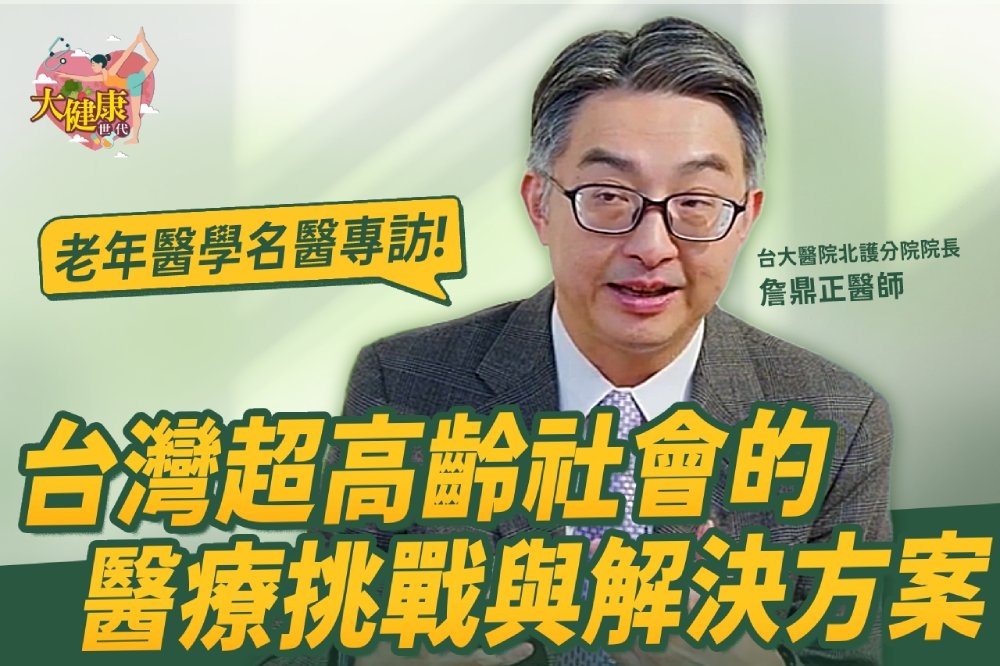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內幕】府院高層520前曾研議內閣局部改組 怕衝擊大罷免才打消念頭 2025-05-24 19:52
- 最新消息 【內幕】政院大刪地方補助燒自家大火 綠營縣市首長收傳真才被告知 2025-05-24 19:50
- 最新消息 外傳美方有意撤出4500名兵力 五角大廈、駐韓美軍出面駁斥 2025-05-24 18:53
- 最新消息 嘉義首次罷免案投票 太保市2市民代表未過門檻可續任 2025-05-24 18:50
- 最新消息 反廢死公投遭否決!藍白齊批民意遭扼殺 綠委諷:是有多巨嬰? 2025-05-24 18:19
- 最新消息 Netflix美劇《星期三》第2季播出日期曝光 凱薩琳麗塔瓊斯、珍娜奧蒂嘉母女相愛相殺戰力升級 2025-05-24 18:06
- 最新消息 美國軍事威脅消失後 葉門叛軍對以色列攻擊力道倍增 2025-05-24 17:48
- 最新消息 捍衛帶手機自由!高中生代表赴教育部抗議 籲退回手機保管政策 2025-05-24 17:31
- 最新消息 《折腰》宋祖兒主動吻上劉宇寧全網暴動 她躺床撒嬌喊「這句話」全網甜暈 2025-05-24 17:00
- 最新消息 看板太多被酸爆!林俊憲逆風挑戰「看板路跑」 跑完自嘲:喝了一肚子苦水 2025-05-24 16:38

歐巴馬當選總統,讓共和黨內原本有能力統合各派的領袖人物 (如小布希)話語空間愈來愈少。(美聯社)
「歐巴馬的當選從根本上改變了共和黨」,這在美國政治圈中曾是個幾經辯證的課題。而這句話實際上存在兩個意義:
第一層意義通常較顯而易見。也就是「左傾意識」的歐巴馬成為美國總統,直接引發共和黨內部激烈反彈,並促使共和黨往極右推進,變得比雷根時期的共和黨還右。當時有一句半諷刺評論:「《平價醫療法案》開啟了歐巴馬時代的共和黨轉型」說的就是在歐巴馬刺激下,共和黨內部原本所謂的中右翼(溫和派)漸漸勢微,表面上,這讓共和黨對諸多議題更易取得共識,實則卻讓黨內原本具備統整跨派系能力的領袖人物(例如2000年勝選總統的小布希、)逐一失去空間,大家必須更旗幟鮮明提出右傾論述,相對才有機會取得有力的黨內話語權。
第二層意義雖然短時間看不出來,不過以共和黨後續發展,其影響亦不亞於第一層意義。即自歐巴馬2008年當選總統後,「適應不良」的共和黨人最積極的反制,就是在國會發動彈劾(總統遭彈劾並被定罪,應予免職)歐巴馬,甚至是歐巴馬才上任數月後就開始,而整個歐巴馬第一任期,共和黨極右派總是不斷努力在尋找彈劾歐巴馬的理由。當時有媒體形容,「彈劾歐巴馬」對共和黨來說,彷彿是一把在尋找釘子的鐵鎚。到後來,「彈劾」先是為了改變選舉(歐巴馬當選)結果,之後則是為了阻止歐巴馬連任。
共和黨一路要求彈劾歐巴馬的理由不一而足,諸如「歐巴馬醫改違憲,強迫美國公民購買醫療保險」、「未經國會批准就宣布對利比亞開戰」、「無視邊境移民危機」等等,再總結為「無法眼睜睜看著一個獨裁政權出現」,更有發起彈劾歐巴馬的組織直接在理由書中稱歐巴馬為「沙皇」(czars)。
但過程中,就算彈劾歐巴馬的民意支持度能夠衝到35%,最核心的問題是,以國會現實,即便讓共和黨掌握參議院多數,參議院也不可能湊到足夠彈劾總統的選票(參議院三分之二席次),為了達到66票門檻,共和黨甚至還得在當年的期中選舉「全勝」才行,實務上更是根本做不到。因此,共和黨提彈劾,他們自己也很清楚,那終究要面臨一個政治問題──鼓動彈劾總統,將帶來選舉紅利還是會疏遠溫和選民?畢竟彈劾總統的高門檻設計,不就是為了阻止人隨意採取魯莽的行動,不讓彈劾總統輕易成為一種政治算計,危害了民主穩固和治理。
既然技術上明知不可行,當時共和黨彈劾派在想什麼卻不是政治學者關切的,因為他們更關切的是,「政客明知不可行而為之的不理性」究竟從何而來?
若根據既有研究,不理性政治行為大致來自四種可能,情節從輕到重為:1.誤判──就像在解答數學問題時計算錯誤;2.無知──對事實認知不足而犯錯;3.價值觀影響──對基本政治價值、信仰存在異常觀念;4.出現非理性狀態──已無法理智討論政治。
其中第四種狀況是最嚴重的,因為在非理性狀態下,通常很可能會同時犯了1、2、3的錯。
回到共和黨彈劾歐巴馬,便有濃濃「4」的味道,否則也不會從歐巴馬上任數月開始催彈劾,彈劾到歐巴馬都順利取得連任了,彈劾派還繼續出版《可彈劾的罪行:讓歐巴馬下台的理由》。
但我們以為「歐巴馬的當選從根本上改變了共和黨」是指共和黨極右化,再因極右化出現非理性狀態,實際發展,卻還有著另一層面的影響。也就是在政客發動的彈劾屢仆屢起始終未果下,再又直接激化了其支持者的沮喪和不滿,最後就是愈來愈多人認為,為了「拯救」國家,「政治暴力」也可以是正當的。
然後,在這樣的認知下,支持者很容易混淆政治「強人」和「狂人」的差別,結果是共和黨的政治狂人川普出現了;其次,在相信「真正的美國愛國者可能不得不訴諸暴力來拯救國家」的共和黨人逐年增加下(三分之一的共和黨人同意),2021年1月6日的國會山莊暴動也登場了。
如今,共和黨從領導人到支持者的形貌改變(極右/容許激烈政治手段),對當下美國來說,對內對外無疑都已帶來了挑戰,這讓當年「歐巴馬的當選從根本上改變了共和黨」一席話,又更傾向是負面形容。只是,當不顧政治道理(訴諸彈劾的合理性)和制度現實(彈劾門檻),就是要「彈劾歐巴馬」的那一刻起,共和黨似乎就沒有了回頭路。
今天的朱立倫說要罷免、彈劾賴清德,會是屬於上述1、2、3、4的哪一項?他日前曾在臉書發文「當民進黨正變成共產黨的形狀...」,那麼,一個身為台灣最主要反對黨的國民黨,在朱立倫手裡又打算變成什麼形狀?
 一個身為台灣最主要反對黨的國民黨,在朱立倫手裡將變成什麼形狀?(攝影:陳愷巨)
一個身為台灣最主要反對黨的國民黨,在朱立倫手裡將變成什麼形狀?(攝影:陳愷巨)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