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是暫時休兵還是偃旗息鼓? 以色列伊朗軍事能力大解析 2024-04-19 22:00
- 最新消息 張忠謀獲頒中山勳章 肯定對高科技產業貢獻 2024-04-19 21:54
- 最新消息 「國家層次」衝突結束? 情報人士:伊朗無意回應以色列攻擊 2024-04-19 21:02
- 最新消息 【強化制海資通】美售台新型野戰資訊通信系統延宕2年 重招商由L3Harris得標 2024-04-19 21:00
- 最新消息 【強化制海資通】透過AI接戰系統整合 讓以岸制海打擊戰力發揮極大化 2024-04-19 21:00
- 最新消息 黃子佼持7部少女不雅片案 高檢署發回北檢續查 2024-04-19 20:44
- 最新消息 「國際金卡納大獎」凱道賽車甩尾對決 19到22日交管一次看 2024-04-19 20:33
- 最新消息 把握好天氣 下周二鋒面接力來襲雨連下6天 2024-04-19 20:16
- 最新消息 竹縣、台東各一議員 6月1日舉行補選 2024-04-19 20:00
- 最新消息 北流1.9億追加案監察院糾正 蔣萬安:一上任積極處理 2024-04-19 19:47

龍應台是喊出了「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喊出了「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那個人,一個可以被西湖的桂花打敗的人。(圖片取自龍應台臉書)
方言
如果方言也不再天長地久,賀知章的《回鄉偶書》還能繼續被世世代代的孩子吟誦嗎?14日下午,淳安女子應美君的女兒、66歲的龍應台在浙江圖書館的報告廳,一次次尋找會方言的讀者,請他們來朗讀她的新書《天長地久》中的片段,這是她寫給93歲、已失憶的母親的信以及大時代的滄桑記憶,其中有她母親的記憶,我聽到了有人用杭州話來念,也聽到有人用上海話來念,尋找山東話的,現場寂靜無人回應,最精彩的當然是美君的兩位鄉人用淳安話來念。
美君的女兒回到故鄉,聽見了母親的鄉音,但她不是少小離家的賀知章,這只是她母親的故鄉。當翻到17歲的美君在日記本上抄錄的王粲《七哀詩》之一,她試圖在現場數百位聽眾中找到最大公約數的浙江方言,引來一片笑聲,從來沒有一種浙江人可以共用的方言,寧紹、溫州、台州、麗水、金華、衢州、杭州、嘉興,各有自己的方言,每一地也有數種不同的方言。
退而求其次,既然是在杭州,想必會杭州話的人最多,誰知會杭州話的竟然寥寥無幾。新杭州人占了壓倒性的多數,一個帶「兒」音的杭州話正在退場,離南宋消亡已740年了。最後她只好請大家一起用普通話來念這首詩中的六句:
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
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詩是1942年抄錄的,也就是電影《一九四二》中河南大饑荒的年頭,中國的抗日戰爭已打了足足五年。「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身為貴胄,卻生逢亂世,先後依附劉表、曹操,活了41歲,詩中所呈現的與饑荒、戰爭、瘟疫困擾的民國31年何其相似,這些詩句毫無疑問曾經引起淳安姑娘美君的共鳴。
今天我們已無法知道這位識文斷字的姑娘是否讀到過當時的《大公報》,1943年2月1日,繼記者發表詳細報導《豫災實錄》之後,主持筆政的王芸生寫下了傳誦一時的評論《看重慶,念中原》,導致罰停三天。當美君塵封的日記被她女兒翻出來,全場以南方口音的普通話讀出王粲的詩,我們也仿佛都回到了1942年。這首詩到底應該用王粲的山東口音,還是抄錄者的淳安口音來念,還真不好抉擇。
方言正在消失中嗎?千餘年來賀知章的《回鄉偶書》之所以引起了廣泛的共鳴,正是因為他寫出了千千萬萬中國人共同的生命體驗,由此上溯,在唐帝國之前的漫長時光中,慢慢積累起來的不同地域的方言、風俗乃至因地理條件形成的飲食等習慣,都曾如此牆固地參與建造了我們的文化傳統,從他往後,一千多年,在農耕文明仍然占主導地位的時代裡,方言的地位都是不可撼動的。
但是工業化、城市化、電視的普及和無遠弗屆的互聯網,所帶來的衝擊,在短短數十年間幾乎重造了一個新國族,尤其以新移民為主體的超大型城市,方言迅速邊緣化,甚至從日常生活中漸漸隱退。我在杭州住了二十多年,兒子上幼稚園就在杭州,可是我們都不會說杭州話,事實上也沒有必要,因為用不著。賣菜的是外地來的,開車的也多為外地的,在茫茫人海中也不大遇到會說杭州話的人。
這樣的變化恐怕是美君那一代難以想像的。我的父親比美君小二三歲,算是同一代人。父親今天還健康地活在自己故鄉雁蕩山的巨石之間,而美君思念了一生的故鄉淳安老城早已消失在千島湖的湖底,這個人工湖過去的正式名稱就是新安江水庫。
1959年到1960年,我的父親曾參與建造了新安江的白沙渡大橋,他一輩子都稱之為新安江大橋,而不說白沙渡。那是一座有252個大理石石獅子的拱橋,當時新安江大壩已截流,美君的故鄉就是那個時候失去的。多少年後,美君即使看到萊茵河,乃至阿爾卑斯山的冰湖,她仍在念叨著:「哪有新安江的水清哦。」這是她頑強得不可改變的童年、少年、青年的記憶。她離開時24歲,戰火即將燒到「溫潤柔美」的江南。
 龍應台在浙江圖書館舉辦《天長地久》新書發表現場。(圖片取自龍應台臉書)
龍應台在浙江圖書館舉辦《天長地久》新書發表現場。(圖片取自龍應台臉書)
故鄉
也許她的記憶就是用淳安的方言存留的。老城可以埋在水底,方言卻隨她終生,與那些店鋪、祠堂以及城門口的石頭獅子一起存在她心裡。當美君告別故鄉的時候,我21歲的父親逃壯丁,輾轉到寧波天童寺打工,目睹了蔣介石、蔣經國的來去,不識字的他並不知道這是一個時代的謝幕,蔣介石到天童寺也是來告別的。
一灣海峽隔斷了數十年的血肉相依。美君的女兒生在臺灣南部的小漁村,聽著母親、父親思鄉的故事長大。這樣的鄉思也成為了她甩不掉的文化記憶。《大江大海》和《天長地久》之間有一條神秘的通道,大而言之是歷史,小而言之是鄉思,但都沒有精準地把握她內心的思量和六十多年的潮起潮落、雲聚雲散。島太小了,母語卻可以擁抱整個大陸。我不知道,是不是母語的力量一次次將美君的女兒帶回父母的故鄉,來親近油菜花和桂花,親近這些她也許聽不大懂的方言。
寫到這兒,我心裡倒覺得踏實了,方言的存歿已屬次要,有《詩經》、《楚辭》、諸子、《史記》在,有唐詩宋詞元曲在,有《三國》、《水滸》、《紅樓夢》在,有魯迅、胡適、錢穆他們在,我們的母語從一開始就超越了地理的限制,當然也超越了方言的限制。
美君的女兒從34年前燃起的「野火」,到今日寫給母親的這些書信,都是在這個脈絡裡生長出來的。她的身上流著那個愛流淚的憲兵連長父親的血液,流著聰慧而有魄力的江南姑娘美君的血液。美君的女兒在65歲之後真的讀懂了她的母親嗎?她迫切地想聽到淳安的鄉音來念與她母親的那些文字,僅僅是想尋找一些心靈的安慰嗎?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她母親故鄉的記憶已沉澱在淳安方言和新安江的水中。她可以踏著燦爛的油菜花,走進湖南衡山她父親的故鄉,如今是父親埋骨的地方,她在那裡可以找蝴蝶兒對語。她也可以一頭撞進西湖邊的桂花香中,瞬間就被母親故鄉的桂花擊敗。當她腳踩在母親故鄉溫潤柔美的土地上,她的眼眶也變得濕潤。那一刻,我明顯地感受到了,她身上兼具了湘妹子和江南女子的兩面,《野火集》代表的是前者,那麼《天長地久》代表了後者。
有水的地方有人,杭州有西湖和錢塘江,是個有碼頭的地方,上游是富春江,再上游就是美君一生念茲在茲的新安江,那水清得哦!今天千島湖的水底依然沉埋著她記憶中的淳安城,曾有人畫出了當年老城的地圖,似乎她家的位置也被標注出來了。與此相比,木頭書包所承載的記憶則顯得溫暖而輕鬆多了。
桂花
借著女兒的筆,美君在93歲之年重新回到了淳安人、杭州人、上海人、溫州人、新杭州人……的面前,此時桂花開得正好,浙江圖書館院裡的丹桂香得讓人不忍聞。而她的女兒在忙著簽書,長長的隊伍一直排到外邊,也許都未來得及聞一聞這桂花香。但西子湖邊,美君口中不斷重複過的桂花,她已聞見。那是白居易、宋之問聞過的,「天香雲外飄」,昔日美君的婚禮是在「天香樓」舉辦的,女兒仍在打聽這樓的消息。
那也是柳永、高濂、張岱他們聞過的,當然也是徐志摩、胡適、郁達夫他們聞過的。那一刻,美君的女兒只是淡淡的一句:「我被桂花打敗」,令人感動。唯有桂花可以穿過唐宋元明清,乃至民國和海峽的阻隔,千餘年來,西子湖頭,有多少英雄豪傑、文人墨客都曾被桂花打敗。想起他們,我就突然明白了,物理時間雖然無情,我們聞到的也許早已不是柳三變的「三秋桂子」,但它一樣可以讓人沉醉,這是一座被桂花醉了千年的城。
無論從威尼斯來的馬可波羅,還是英倫來的馬戛爾尼一行,乃至生於斯長於斯的司徒雷登,面對桂花,恐怕都不會無動於衷。我們活在同一個人類的精神譜系裡,一個可以超越語言、種族、膚色和宗教信仰的譜系裡。物理時間的無情,與有情的人類世界相比,實在太微不足道了。這是愛因斯坦回答不了的問題。
「美君的女兒」,這話一出口就讓滿城流淌著桂花香味的杭州,對於她這位在海峽另一邊相隔十年才來一次的女兒,不再浮在空中,而是踏在地上,溫潤柔美的地上,一下子就與我們站在了一起。
人性
在龍應台《天長地久》讀者見面會的現場,我寫了幾句話:
相隔十年,淳安姑娘美君的女兒又來了。這次是為新書《天長地久》的讀者見面會。上次是為《大江大海》收集材料。歷史千迥百轉,一切皆在尋常人性之中。時代可以破碎,人性需要溫暖。大起大落的家國動盪,擋不住人心深處的嚮往。
天長地久,世間有什麼才配得上這四個字?人性所包含的親情、友情、愛情,它們所代表的人類情感,透過中國人的《詩經》、希臘人的《荷馬史詩》或希伯來人的《舊約》,我們不是一次次地看到——物理時間無情的流逝,但我們同樣看見了時間無法摧毀的「呦呦鹿鳴」、「楊柳依依」、「桃之夭夭」,看見海倫在特洛伊城頭出現的刹那,看見郝克托爾與妻子的話別,看見大洪水之後的那道彩虹和西奈山上的閃電……
美君的女兒帶著《野火集》在三十幾年前掀起的「龍捲風」,曾經吸引過我的青春歲月。那是1987年,我的老師吳式南先生正在壯年,將「胡美麗」1985年發表在《中國時報》的《美麗的權利》《不像個女人》油印給我們。隨後,《野火集》在大陸問世。我買過幾個不同的版本。我知道,這些雜文屬於年輕時曾住在杭州、也聞過桂香的魯迅這一譜系的,但她在成長過程中並未讀過魯迅,在她出生之前,國民黨當局就將魯迅的書統統變成了禁書。
1949年10月31日,陳誠簽署的「臺灣省政府」訓令《公佈反動思想書籍名稱一份》,附有《反動思想書籍名稱一覽表》,下發給各縣市政府、各級學校、各社教機關,其中文藝類被禁的書包括《魯迅全集》《魯迅書簡》,以及關於魯迅的回憶和傳記,包括蕭紅《回憶魯迅先生》、孫伏園《魯迅先生二三事》、林辰《魯迅事蹟考》、範泉譯的《魯迅傳》,禁得很徹底。(參考傅國湧《臺灣禁書小史之一》)
少年時與魯迅無緣,到美國留學才接觸到魯迅作品的龍應台,她立言的基礎是普世常識,是基於人情、人心、人性,剛猛的背後其實藏著一種柔情。只是當時不容易讀出來。她寫那些文字正好在「解嚴」之前,她抨擊社會痼疾,既是出於人之常情,也是人心所向,激起了社會的巨大反響。「野火」之後,我讀到的是《龍應台評小說》,也是吳式南老師推薦的。前些日子,我去九山湖畔看他,86歲的先生還跟我說起這本書。三十年過去了他還是一口好評。
從《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開始,她的作品就開始觸及父輩的傷慟和記憶、思鄉的美好與痛苦。等到這本《天長地久》,轉眼十年過去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面對的是時代的劇烈變動,一個歷史的大裂口。此前四年(2005年1月),我的《1949年:中國知識份子的私人記錄》即已問世。她從雜文逐漸轉向非虛構敘事,文學性還是很強,同時帶有她個人的獨特生命體驗,特別是她父母那一代人深入骨髓的記憶。我忘不了南下逃亡的學生顛沛流離,一路上帶著那本唯一的《古文觀止》。
尊嚴
守護那些秦漢論賦、唐宋文章,就是守護源遠流長的母語傳統,《古文觀止》一卷在手,我們就有依靠。即使在她乾淨的白話文背後也依然可以讀出《古文觀止》的千絲萬縷來。
對於她的作品,我更偏愛的還是《請用文明來說服我》中的文字。中文世界,如果要在白話文一百年中選出一百個人,而一個人只能選一部作品,在影響巨大的《野火集》和大陸讀者陌生的《請用文明來說服我》之間,我還是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
那是乾淨、明白的中文表達乾淨、明白的思想,不在魯迅的雜文譜系裡,也不在張季鸞的時評譜系裡,而是在一個新的譜系裡。
如何重建母語的尊嚴?這本以非虛構敘事為主的隨筆集提供了美好的範例。中文世界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就藏在自己的母語裡,這是從胡適之他們的精神譜系中生長出來的。我曾說,魯迅是酒,胡適是水。胡適明白、樸素、講常識,《請用文明來說服我》中的不少文章曾在《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和《南方週末》發表,比如《你可能不知道的臺灣》《文化是什麼》等。這些文字像水一樣清楚、水一樣的透亮。美君的女兒也曾是火,三十年後化為了水。
這一晃又是十多年過去了,面對《天長地久》,從現場聽眾所提出的問題看,幾乎多為《目送》《孩子你慢慢來》《親愛的安德列》這「人生三書」的讀者,熟悉《野火集》的人已不多,熟悉《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更少,至於讀過《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則少之又少了。將這些書放在一起,才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龍應台,她當然是美君的女兒,也是喊出了「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喊出了「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那個人,一個可以被西湖的桂花打敗的人。
2018年10月15日寫於杭州國語書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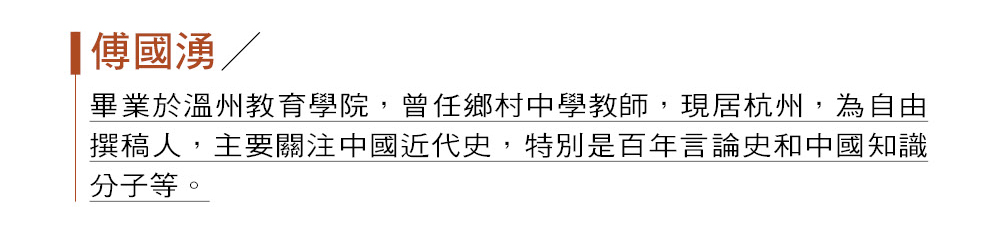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淚之女王》金智媛、金秀賢互飆演技收視破20% 「洪海仁墓碑」劇照瘋傳網憂BE結局
- 《蓮花樓》成毅新劇高馬尾造型曝光帥翻 憑2關鍵奪回藝名聲勢輾壓師兄任嘉倫
- 【《承歡記》內幕曝光】楊紫片酬拿2億演技卻被罵翻 許凱演霸總9千萬輕鬆入袋
- 《與鳳行》林更新公開女友惹怒CP粉 趙麗穎親上火線17字幫忙救場超暖心
- 《慶餘年》第二季5月播出全網沸騰 「他」接演肖戰角色2關鍵被看衰
- 【韓星片酬大公開】金秀賢拍《淚之女王》因「這理由」降價演出 IU身價輾壓宋慧喬
- 肖戰新劇凝視《惜花芷》張婧儀畫面曝光甜出汁 新片與《在暴雪時分》趙今麥演兄妹超吸睛
- 白敬亭拍趙露思《偷偷藏不住》姐妹作制服照曝光 「這關鍵」帥度不敵陳哲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