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陳嘉宏專欄:這不是「不藍不綠」 這是「圍事小弟」 2024-04-24 07:02
- 最新消息 張惠菁:在「自由的窄廊」裡決定死刑的存廢 2024-04-24 07:00
- 最新消息 《大家論壇》共榮視角:投資全球公共財 協商出大而美的世界銀行 2024-04-24 07:00
- 最新消息 必勝客披薩母親節 64 折!「壽星最大盒」驚喜登場 披薩、拼盤、巴斯克蛋糕一次滿足 2024-04-24 07:00
- 最新消息 自爆台北慈濟患者遭偷拍、下體瘋狂被搓揉 具名檢舉護理師10萬元交保 2024-04-23 23:30
- 最新消息 【誰有決定權激辯】廢死釋憲方力陳民主應有界線 死刑合憲派主張宜交立法權抉擇 2024-04-23 23:27
- 最新消息 新聞分析/廢死釋憲結果如何繞過民意 將成賴清德首道執政課題 2024-04-23 22:40
- 最新消息 【火藥對槓】不滿法務部牽拖民意反廢死 詹森林連珠炮犀利問「難道要大法官捨棄憲法價值?」 2024-04-23 22:30
- 最新消息 【有片】西班牙增購NASAMS防空系統 提升反飛彈、空防能力 2024-04-23 22:00
- 最新消息 地震重創觀光業 花蓮旅館同業公會:損失上看20億 2024-04-23 21:47
「自由」二字的堅持,起碼給後來的民主台灣預備了一個基本否定獨裁的共識。(圖片擷取自Youtube)
十年前,據說大陸一度叫停「自由行」這個詞,因為裡面「自由」二字太令人浮想聯翩,顯得選擇「自由行」方式去港澳台旅行的人都像投奔自由似的。有的旅行社不識趣,改叫「自遊行」,那更是犯了大忌,你要去海外遊行示威?最後定下叫「自助遊」,和「自助餐」一個級別—也是提醒出國的人民,不要想多了,你不過是在離境消費而已,並非去享用自由。
但是「自由行」這個詞,始終無法在民間抹去,無論是大陸要出來的人還是海外接待這些人的人,下意識還是使用「自由行」來自稱或稱呼這些並不自由的遊客。在應亮名為《自由行》的電影裡面就可見,不但那團來高雄「自由行」的大陸遊客的行程並不自由,一路追隨以求和團中母親短暫同行的流亡導演楊樞也不自由—即使她已經為了得到自由捨棄了很多。只有那隻製造不自由的魔掌是自由的,它可以伸進每一個人心中製造恐懼,使母親只能選擇犧牲、女兒只能選擇憤怒。
我在異鄉、台北的電影院裡看著這部電影,也是悲憤的。中港台三地的流離,都取決於電影中那個隱形的力量(它並沒有一個具體角色代表,甚至連電話裡的畫外音都沒有,卻無所不在),它反對著最基本的人類關係:家庭。我們以為一家團聚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到它手裡這是恩賜、是籌碼、是勒索。
電影裡最打動我的對白,是楊樞最後對追問她身份認同是大陸人還是香港人的時候,她回答的一句:「我是異鄉人」—一個藝術家就是永遠的異鄉人,直接把什麼國族pass掉,也一下子解開了電影大半部她的彆扭。
我想到剛剛在香港去世的詩人孟浪。他的半生漂流,壯志未酬,他的詩歌與精神是自由的,但肉體卻消耗在與荒謬之力的搏鬥中,他因為愛這個國而被迫與家分開——這幾乎是每一個流亡者的宿命。如果不愛,也就無所謂了。也許《自由行》裡的楊樞和應亮這一代流亡者能夠以不屑代替愛,以拒絕選擇來超越對國家與民族的執著,才能重建一個人的自由。
香港至今仍能容留流亡者,雖然這個容留的尺度比起五六十年代、甚至清末,都已經大大收窄。不變的只有民間的人心,流亡導演楊樞的香港人丈夫,他自己一個人代表著整個香港的道義精神,現實中應亮的妻子並不是香港人,因此前者可以看做是應亮流亡中所遇到的所有幫助、支持他的香港人的一個象徵。這個象徵過於完美,然而現實中真的有過這樣的香港人,義字當頭,更何況,還有情。
另一個自由的承載者,是台灣。不要忘了,幾十年前,台灣還有一個名字,叫「自由中國」,且不論有多少名實相符,是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這「自由」二字的堅持,起碼給後來的民主台灣預備了一個基本的否定獨裁的共識。有雷震等人的堅決,然後有美麗島的崛起、野百合的燎原。《自由行》電影裡僅僅以在團中尋親老人的講述中存在的那一個台北被槍斃的親人,代表了在也不自由的「自由中國」裡湮沒的一代犧牲者。
而台灣對這部電影的承擔,不是出現在電影裡面(電影裡只是以各個計程車司機去表述了台灣眾聲喧嘩的政治面向),而是出現在電影製作本身。高雄電影館「高雄拍」計劃對應亮的資助、電影製作團隊裡佔大多數的台灣人對這部敏感電影的支持,這都讓人難以想像是一件發生在要和「中國」積極切割的台灣的事。
當然,自己的國家自己救,這部電影最讓我敬佩的,是那些大陸演員,包括演母女的耐安和宮哲,也包括演大陸遊客的所有應亮的朋友。她們在明知這部片會被大陸禁止,也可以預想自己可能因為參演此片會遭遇或多或少的麻煩,依然挺身支持應亮,這不光是為了藝術,也是自己心中的一股正氣的宣示,拍了就拍了,問心無愧。
如果我們還覺得我們身處自由之地,覺得自由是天經地義的話,我們應該買票進影院去看看這部電影,看看有多少不自由在虎視眈眈等著我們,又有多少自由需要我們去栽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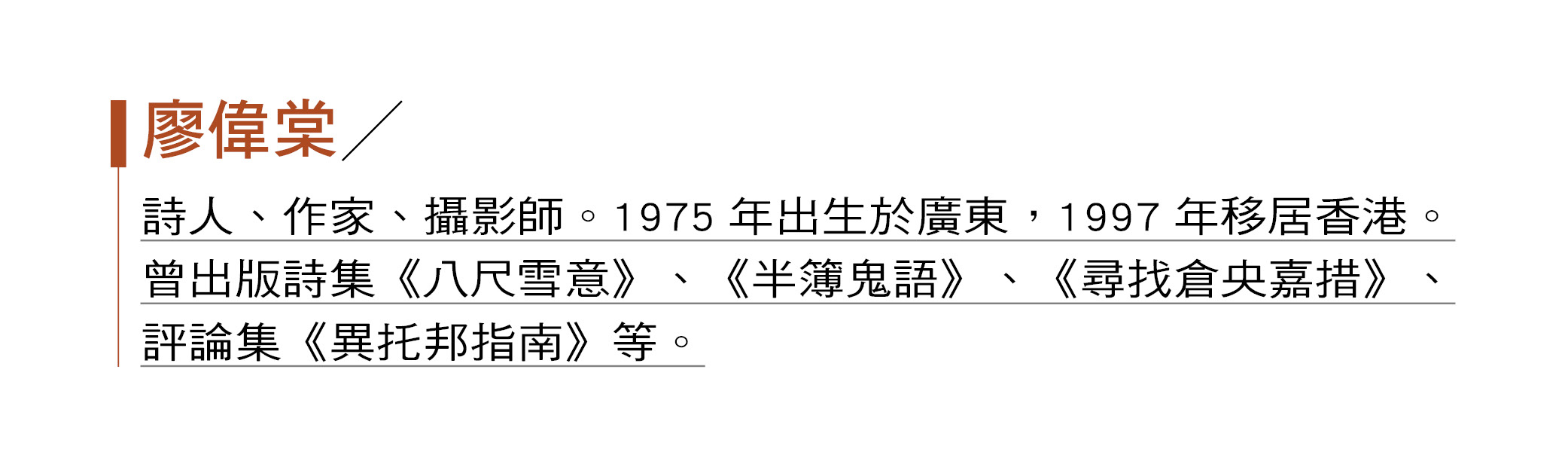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淚之女王》金秀賢逼哭觀眾迎來出道第3次爆紅 寵溺金智媛超甜蜜收視超越《愛的迫降》
- 投書:如果F15EX能加入台灣空軍
- 《不夠善良的我們》林依晨不忍賀軍翔婚姻冷暴力 「簡慶芬出軌」演技大噴發掀淚海
- 最多現省 486 元!拿坡里披薩、炸雞「買一送一優惠」只到月底 12 塊雞腿、腿排只要 399 元
- 《慶餘年》肖戰大學受封校草青澀帥照曝光 他因「這理由」不敢發自拍全網笑翻
- 《長月燼明》白鹿新劇搭檔《蓮花樓》曾舜晞爆不和 他「妝造醜翻」疑遭打壓粉絲氣炸
- 《去有風的地方》劉亦菲現身LV大秀「裙子像鋼刷」遭群嘲 卻因這理由反轉負評好感狂飆
- 麥當勞買一送一!10 塊麥克雞塊、薯餅、焦糖奶茶通通有 歡樂送買一送一、深夜食堂享 79 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