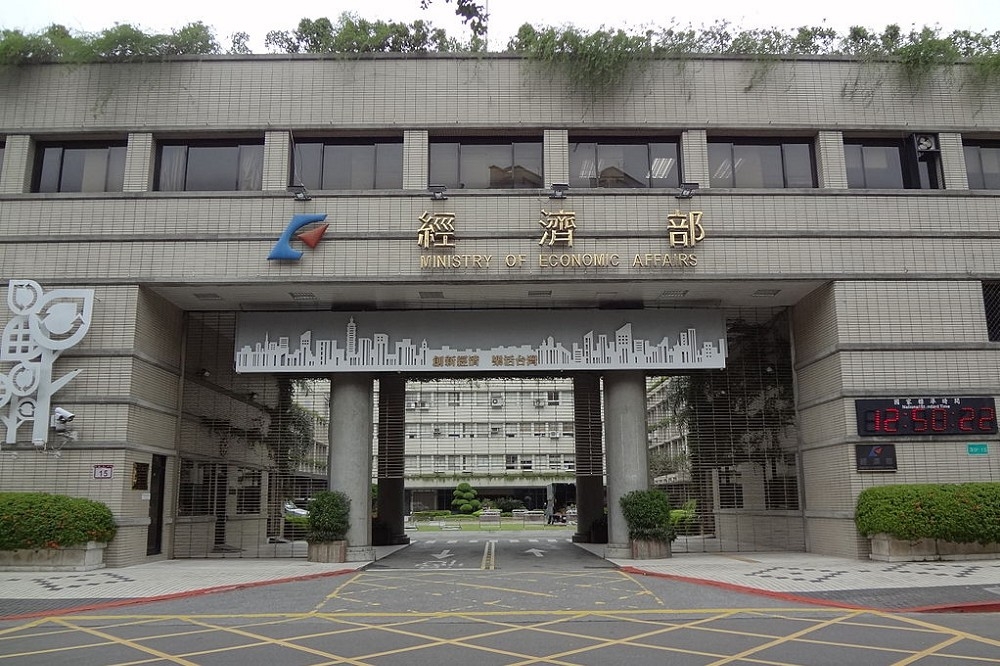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曼迪春日動漫祭插旗中山!買柯南周邊贈電影收藏卡 海豹小白快閃店同台登場 2024-04-24 12:00
- 最新消息 台股飆漲重返2萬點大關 台積電一路漲最高至784元 2024-04-24 11:50
- 最新消息 俄國副防長涉貪被捕 疑為防長去職前的肅清行動 2024-04-24 11:35
- 最新消息 羅雲熙、宋軼新劇《顏心記》大婚場面預告曝光 兩人甜擁放閃全網呼叫白敬亭 2024-04-24 11:20
- 最新消息 【死刑論辯】廢死聯盟形容死刑如「殺人機器」 直言:不應被修補、應該銷毀 2024-04-24 11:10
- 最新消息 台灣恐發生規模8.7強震? 地震專家馬國鳳怒轟「錯誤報導」 2024-04-24 11:05
- 最新消息 不只 7-11、全家!萊爾富「哈根達斯買 3 送 3」限時開賣 2024-04-24 11:00
- 最新消息 【廢死論辯】法務部堅持死刑合憲 蔡清祥:廢死是另一個問題 2024-04-24 10:49
- 最新消息 成毅新劇虐戀李一桐預告曝光400萬人爭睹 他白髮揮舞火劍帥度超越《蓮花樓》 2024-04-24 10:40
- 最新消息 美參院通過軍援烏以台、強制TikTok分拆法案 拜登將儘速簽署 2024-04-24 10:28

臺灣媒體對政務官在媒體上撰寫社論與專欄從未避嫌,執筆的官員也不以為意,長期以來為媒體寫社論非獨管中閔。(攝影:鄭宇騏)
有人說,報紙的社論有如人臉上的眉毛,用處不大,最多是汗流如雨時,擋住汗水進入眼裡,最大的作用,還是美觀。然而,如果缺了眉毛,不僅顯不出眼睛的神采,也恰似一幅圖畫,留白太多,單調而無韻味。報紙的社論雖是一家之言,但影響力多大?有多少讀者認真細讀?答案不問可知,但如果取消了社論,卻像刮掉了眉毛,怎麼看都不順眼。
為媒體寫社論非獨管爺
最近監察院小題大作,對臺大新任校長管中閔提出彈劾案,指他任官期間曾為壹周刊撰寫社論,並用筆名為其他刊物撰寫專欄,有違法之嫌。政務官能否在媒體上撰寫社論與專欄,的確是可議之事,尤其是寫作內容如涉及所主管的業務範圍,不論是支持或反對某項政策,都有道德上的瑕疵。但是臺灣的媒體對此從未避嫌,執筆的官員也不以為意,因此大批官員在媒體上放言高論,已成常態,如果監察院要對此提彈劾案,就不能針對管爺一人下手,一旦全面篩檢,勢必有更「驚人」的發現。
我任職報界四十餘年,主管「修眉」的工作斷斷續續也有三十餘年。各報的主筆群中,學者或大學教授佔最大比例,其次為社內的專任主筆群,再其次就是政府官員。官員中比例最高者乃財經部門,其次為民代與科技、環保與衛生等單位官員,行政官員與法官則絕無僅見。
上述部門,專業性較高,需要理論與實用並濟,主管其事者多由學者轉任,不僅專業學識深厚,在務實應用與制訂政策方面亦多有獨創的見解,只要寫作的內容不脫離現實太遠,並與報社的立場不背道而馳,都會受到歡迎。這類文章既非學術論文或高頭講章,亦無明顯的政治色彩而作攻擊之論,深入淺出,平白近人,故看不出是高官之筆,大部分亦言之成理,提供極具價值的意見,供政府參考。
財經官員寫社論頗受歡迎
我於1988年自美返臺,任中國時報總主筆,前任是楊乃藩先生。他文筆極佳,延攬之寫手亦均一時之選。斯時財經方面的社論皆出自王作榮與汪彝定先生之手。王先生於1978至1988年十年間,擔任工商時報總主筆,1984年同時擔任考試委員,也算是政府官員了。他在中時及工時所發表的社論及專欄,見解超人,提出一系列的政策主張,多被政府採納,以致天下雜誌譽他為「第一位政策經濟學家」及「經濟設計師」。
他主張,承平時代,政府應放手讓經濟自由發展,少插手其間,但在經濟發展遭遇世局影響,面對困境之際,政府亦應扮演適當的管制角色,不能過度放任自由。此一理論經他反覆詮釋,政府主管財經、貿易官員都能誠服接受,肇致臺灣七、八十年代的經貿發展一路順風,王作榮先生堪稱是最佳舵手。而中國時報的社論亦因此聲譽鵲起,由「眉毛」升級為「眼睛」了。
另一經貿作者汪彝定先生才華橫溢,文采多姿,除財經題材外,亦兼寫一些社會問題,因見解超然,語多幽默,極受讀者歡迎,他那時任職國貿局長,如以現在監委的執法標準,他亦應遭到彈劾。
我接任後,王作老(我們都這樣稱呼他)因年邁不再寫稿,然而他老當益壯,1990年還出任考選部長,1996年又出任監察院長,當然也沒有精力再寫社論。汪彝定先生在1989年左右罹患癌症,開刀、吃藥、打針,受盡折磨,但在如此的身體狀況下,他仍應允撰寫社論。由於全身疼痛,竟趴在地上寫稿,其精神令人敬佩。但細讀其內容已大不如前,諸多段落必須重加潤飾,後因體力大衰,也就不再執筆了。
此時為中時寫財經方面社論的主筆,其一是政大教授殷乃平,另一是陸委會經濟處主任傅棟成先生,傅先生是王作榮的學生,也是王力薦到時報擔任主筆撰稿者。他寫稿平實、簡潔,見解不凡,尤其是有求必應,無論多麼忙,只要一通電話,他必然準時達成任務。某次他打電話至報社,表示因為工作繁忙加之寫作壓力,寫到一半竟然暈倒,文章難以為繼,我聽後大吃一驚,請他家人立刻將已寫竣的部分傳真到報社,由我狗尾續貂,勉強湊全,次日問社內同仁都說看不出接縫的痕跡,我總算放了心。他的用心與敬業,實令我感動,迄今難忘。
中時「主筆」達七十餘人
另一難忘的主筆則是王建煊先生。他於1990年6月出任財政部長,但仍為工商時報撰寫社論。91年某日,余紀忠先生問我為何不敦請王部長也為中時寫社論?我當然立刻遵命,先求見王部長,並在來來飯店二樓設宴請他吃飯,談談寫稿事宜。在座作陪的,還有劉必榮、黃輝珍等主筆,席間我請教他:「部長希望寫哪一方面的專題?我需將社論內容與新聞配合。」他答曰:「都可以!什麼題材都可以。」我聽後頗為吃驚,每個人都有其專業範圍,尤其現代化的臺灣,分工極細,懂財經不一定懂法律,懂法律不一定懂外交,懂外交不一定懂醫衛,怎麼有膽說:「什麼都可以?」
過了幾天,我終於找到適合的題目請他執筆,他倒是一揮即就,社論一般約晚間十時左右截稿,他居然七時許即寫畢交稿。我讀後大吃一驚,在此不細述其內容,只覺得必須面呈老闆,決定取捨。我先安排一篇備稿,再攜王稿晉見,未料余老闆該晚赴忠孝東路某友人家打麻將,我問得地址,先電話聯絡,再叫計程車直奔該宅求見。
余先生真是一位盡責的報老闆,他立刻停牌,到客廳與我相見,我呈上王部長的稿子請求定奪。他認真讀了以後,面孔緊繃,小聲說:「不能用,不能用,你有無備稿?」我說:「已有備稿,無庸耽心。」他再說:「叫他以後不要再寫了。」哇!我知道他不便直接向王開口,壞人由我擔當,我也只能硬著頭皮,以電話向王解釋,並致上無限歉意。這一段公案就到此結束。
次日下午,余先生約我到他的住處,問我處理的方式,並拿出一本名冊,要我細看一下,這本名冊封面寫的是:「中國時報外聘主筆年資及薪資表」。打開一看,竟有七十餘名主筆,薪資最少者每月為兩萬五千元,最高者有七、八萬元。我再細看,其中為我們長期寫稿者僅六、七人,其他均為掛名主筆,支薪而不寫稿。名單中洋洋灑灑,有內政,有外交,有司法,有教育,當然更有財經諸官員。顯然這是余老闆拉攏在朝官員的一種手法,尤其薪資一律以現金支付,俾不著痕跡,「王聖人」亦名列其中。
表面上看,不少官員多方設法與媒體建立關係,實際上,媒體負責人也多方設計,希望從政府官員處得到若干無形的支援,包括人事的安排與財務的挹注。以臺灣日報老闆傅朝樞為例,他因與王昇有同鄉關係,與蔣彥士也有特殊私交,雖然沒有找他們為報紙寫稿,但各種私下的往來不時可見於新聞版面。所以臺灣日報社被迫賣予總政戰部後,竟可將交易所得全數結匯,寄至美國。在那個戒嚴時代,能獲得如此特權,若無相當政商關係,何能致此?
社論宣示報老闆的政治立場
社論有無重要性,老闆與總主筆之間往往有些不同的想法,老闆認為,這個一、兩千字的長形方塊,是代表他個人立場的園地,除了宣示政治立場與主張,往往也藏著私人的恩恩怨怨。字裡行間隱藏著許多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不足為外人道者居多,而總主筆雖有主觀的思想體系,若與老闆的想法扞格,往往也只能遷就老闆的想法。我常公開自我調侃:「總主筆正式的名稱應該改稱『代書』,總主筆只是一個好聽的名詞而已。」
我服務過九家報紙,伺候過六位老闆,主持社論工作者達八家,其中最尊重總主筆與寫作群意見的老闆有兩位,一是高雄臺灣時報(以及美國遠東時報)的吳基福先生,一是中國時報(包括美洲中時)的余紀忠先生,尤其余先生高倡自由主義,除了重大新聞事件外,很少過問社論寫作的內容與方向。但遇到關鍵性的重要議題,他不僅字斟句酌,一看再看,甚至要求重新寫過。記得郝柏村組閣的那一次,國人的看法兩極化,有人認為軍頭組閣,必然將臺灣的民主拉至反方向,再度回到國民黨集權的時代。
康寧祥主持的首都早報,竟然整個頭版版面僅用了一個「幹」字表達心聲。那天晚上,余老闆到了編輯部,坐在我的對面,要求我每寫一張即交給他審核。老闆就坐在對面,一頁一頁地審稿,其壓力之大,不堪想像。我只能硬著頭皮寫一頁送一頁,終於大功告成,左右同事都斜眼偷覷,看我怎能在這種情況下,還能從容完稿。
冒犯老闆 社論無法見天日
當然,這種場面,我任職中時八年中,僅此一次,但凡涉及政治上的政策、人事變遷或重大弊案,他都會特別關心,並要求看稿。1992年,簡又新先生任交通部長,任內發生了「十八標案件」,起初只是立委葉菊蘭在國會質詢,暗示有五位國民黨立委在高速公路十八標案中,收取鉅額賄款,立委及記者數度詢問簡部長,簡一律笑而不答,顧左右而言他,無形中增添更多的神秘感。
後來案情發展愈演愈烈,不僅監院主動調查,甚至地檢處與調查局亦派員介入,交通部乃主辦單位,部長怎可用笑而不答或「不作評論」敷衍塞責,於是我撰寫一篇社論,要求簡部長必須釐清案情,主動出面說明,怎可抱持「和稀泥」的心態敷衍,大事化小?此稿寫成後,我心知該事牽扯甚廣,主動到老闆辦公室呈閱。他細讀後不發一言,直接打開桌中抽屜,將稿子置入,關上抽屜後,對我一笑,只說了一句話:「書生之見」。然後叫我趕寫備稿。我當時一頭霧水,這件事怎麼扯得上「書生之見」?事隔數天後,我終於了解,他與簡私交甚篤,不願以十八標案指摘交通部長,甚至次日竟將原稿私送簡又新過目,討個人情,幸好稿上未留姓名,否則我豈不是平白惹上麻煩。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1992年。那時蔣經國已過世,李登輝繼任總統,余先生曾在中常會擁立有功,加上王作榮先生極力牽線,李、余之間也發展出相當的情誼。我斟酌當時情勢,寫了一篇社論,主張裁撤救國團,或者改為教育部轄下的青年活動組織,以與國民黨脫鉤,避免淪為「青年洗腦機構」。此稿呈閱之後,亦遭到同樣命運:一聲「書生之見」後,置入抽屜之中,永未再見天日。
綜而言之,臺灣媒體的社論、專欄,操刀者以學者為最多,媒體人次之,政府官員、尤其是財經官員亦不少,他們固然賺了不少稿費,但也對國家制訂政策作出不少建言,當然也有官員利用為報紙撰寫社論而牟取私利者,如某教育部官員為中時撰寫社論,當自身晉升為國際文教處長時,寫了一篇自我吹捧的社論,題目竟然大書:「深慶得人!」余老闆閱後表示,天下竟有這麼不要臉的人嗎?一邊說著,一邊將稿子撕得粉碎,擲入字紙簍中,我們都大笑不已。
人間事有利有弊,我始終堅持一種看法:「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官員寫文章似無不可,只要不「深慶得人」,就不算是踰閑了。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服役後,考入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與故宮博物院合作的中國美術史專班。畢業後,進入故宮博物院任助理研究員,從事藝術研究工作三年半,後轉至新聞界,曾任:臺灣時報總編輯,臺灣日報總編輯。1979年赴美,曾任:舊金山遠東時報總編輯,紐約中報總編輯,紐約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總主筆,紐約北美日報社長。1987年返台,任中國時報總主筆,1996年轉任自由時報副社長。2014年退休。作者見證過去近50年台灣新聞史,《編輯台憶往》為其記者生涯的回顧,獨家於《上報》連載。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淚之女王》金秀賢逼哭觀眾迎來出道第3次爆紅 寵溺金智媛超甜蜜收視超越《愛的迫降》
- 投書:如果F15EX能加入台灣空軍
- 《不夠善良的我們》林依晨不忍賀軍翔婚姻冷暴力 「簡慶芬出軌」演技大噴發掀淚海
- 最多現省 486 元!拿坡里披薩、炸雞「買一送一優惠」只到月底 12 塊雞腿、腿排只要 399 元
- 《慶餘年》肖戰大學受封校草青澀帥照曝光 他因「這理由」不敢發自拍全網笑翻
- 《長月燼明》白鹿新劇搭檔《蓮花樓》曾舜晞爆不和 他「妝造醜翻」疑遭打壓粉絲氣炸
- 《去有風的地方》劉亦菲現身LV大秀「裙子像鋼刷」遭群嘲 卻因這理由反轉負評好感狂飆
- 麥當勞買一送一!10 塊麥克雞塊、薯餅、焦糖奶茶通通有 歡樂送買一送一、深夜食堂享 79 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