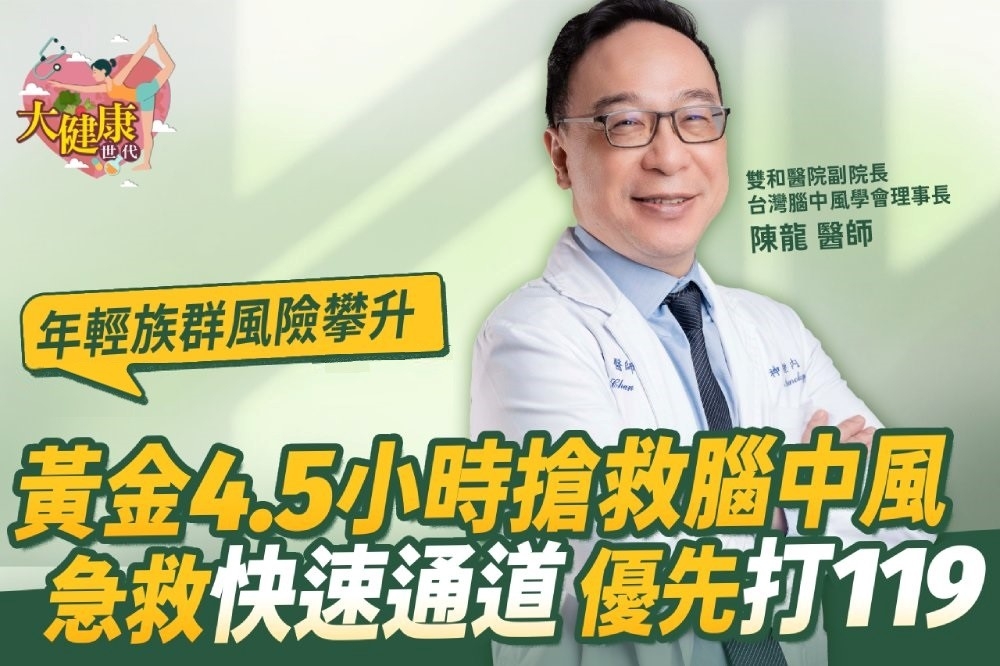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川普大規模減稅連自家人都不挺 馬斯克坦言「感到失望」 2025-05-28 20:58
- 最新消息 教育部封殺中國「國防七子」 鄭英耀:我拍板決定的 2025-05-28 20:57
- 最新消息 黃安主張武統被撤銷國籍? 網友嗨喊「大快人心」、陸委會說話了 2025-05-28 20:45
- 最新消息 台東一名男童戲水被沖往海口 釣客跳水營救雙雙失蹤 2025-05-28 20:12
- 最新消息 網友涉造謠「陳菊走了」遭送辦 法院裁定不罰理由曝光 2025-05-28 19:49
- 最新消息 北檢主任檢察官票選結果出爐 柯文哲案主力唐仲慶、林俊言分獲第1及第6 2025-05-28 19:16
- 最新消息 俄集結5萬兵力恐發動夏季攻勢 普丁擬要求西方承諾北約不接納基輔 2025-05-28 19:04
- 最新消息 【懶人包】新冠疫情6月恐飆高鋒 「症狀轉變、疫苗接種、快篩使用」一次看懂 2025-05-28 18:50
- 最新消息 馬克宏訪印尼拚軍售 簽防務協議有望加碼賣戰機潛艦 2025-05-28 18:21
- 最新消息 AIT外籍人員開車撞老闆娘喊「機密」! 7天後才現身道歉 2025-05-28 18:18

「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1990年3月16日,9名台大學生於台北市中正紀念堂外「大中至正」的牌樓下拉起了白布條,靜坐抗議將近半世紀未曾改選的七百多位資深國大代表,拉開野百合學運序幕。(攝影:蔡明德)
今年(2020年)甫開始不久,卻無疑足以被認為是風起雲湧的一年:臺灣在年初經歷了第七次的總統大選與國會改選,現今又面臨新型冠狀病毒傳染病的威脅,在這樣緊張的社會氛圍下,讓人不自覺地忽略了2020年所具備的另一個歷史意義──這是野百合學運爆發的第三十週年。
1990年發生的野百合學運,作為臺灣解嚴後第一場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對於臺灣的民主體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也對後來臺灣學運樹立了某種程度上的典型。如何評價野百合學運在政治或社會層面造成的影響,早已是無數報章雜誌或學術文章討論的議題,與當時參與野百合的學生差不多年紀的我們,需要思考的是,我們從野百合學運中能夠看見什麼?而這樣的歷史經驗對於當今大學生們又有何意義?這一點之所以重要,在於當校園中對政治的談論或參與,已不再被法律的強制力明確禁止時,掌權者們選擇以其他的形式限縮這些自由,如對空間使用權的規範、對決策程序中學生代表人數的限制等等,這些新的治理型態與手段,使得學生在校內爭取權益的過程中,面臨了新的困境。
在這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籠罩下,這種狀況也出現在大學的防疫管制中,無論是學生社團活動的無預警喊停、對校園進出的嚴格管控、或是校級防疫會議中學生代表的缺乏,皆彰顯了校園中校方與學生的權力關係,仍然呈現極度不對等的狀態。類似的情形實際上在校園內反覆上演,只是在校園的防疫措施中才格外明顯,學生長期以來在校園中的弱勢地位,並未被全體學生們廣泛地意識到,原因正是校方在有限度開放校園民主的同時,卻仍然透過上段提到的方式限縮學生參與的程度,並且在掌握詮釋權與傳播工具的情況下,用這種表面的開放參與,來掩蓋權力不對等的事實。隨著壓迫不再清晰可辨,而是以更加迂迴的形態出現在生活當中時,學生該如何辨識這些壓迫的存在,並匯聚起學生的政治能量,嘗試能夠有效反制與協商的手段,成了迫切的問題。
野百合學運發生的前夕,參與核心決策的學生們,不少便是在學運發生前,就持續在推動校園內民主的行動者,他們從在校內的耕耘累積起經驗,到後來組織起一場大型學運,這其中的經驗或許能夠給我們一些啟發。這樣的啟發並不在於單純複製他們的方式,而是在其中觀察他們如何組織起學生,也同步關注其他學生的參與如何影響了運動中的決策過程。在當今抗爭性活動愈來愈限縮於小部份人,並難以獲得其他學生們普遍的響應的同時,不難發現兩群人間的交集愈來愈少。在這樣的情況下,如野百合學運這樣,能夠匯聚起眾多學生們的政治能量,對掌權者施加壓力的大型抗爭活動,究竟在當年的時空背景下如何發生,又呈現出立場或主張不盡相同的學生之間,存在著哪些互動的模式和樣貌。
在這一系列對於野百合學運的回顧文章中,我們透過對參與者們的訪談,以及過去相關的報導、書籍或回憶錄,逐步拼湊起關於野百合學運的新敘事。從爆發前夕校內各式的學生活動中,觀察學生們如何進行組織,將民主理念推及到校內,而各個不同行動者或組織間又如何集結;接著,在野百合爆發後,廣場內部的學生們如何協調權力,各種決策在這樣的角力中又如何形成,並試圖從退場過程中,進一步審視這樣的決策過程中帶來的影響,並觀察當年參與者們事後如何持續推動校園內的民主參與;最後,我們藉由野百合學運中的經驗,來反思當今校內民主所面臨的困境,並思考校園民主的更多可能。
(本專題由臺大學生會新聞部共同採訪完成,並由部員分別進行撰稿,感謝部員蔡硯涵、江姿葶、吳培鎰、涂景亮、廖彥甄、陳勝發、卓庭安、陳曼琳、吳東憲、林哲如協助採訪。)
被壓縮的民主:校園的掌控與限制
今日的我們回頭看八零年代的臺灣,可以說那是一個民主化與本土化紛紛萌芽的時代,先後歷經了美麗島事件、中壢事件、民主進步黨的成立,社會改革聲浪達到頂峰;相較於黨外活動的興盛,威權體制下的校園,卻在黨國思想的嚴密箝制下被迫噤聲。曾因學運失利的國民黨非常清楚學生動員的力量,擔心學生運動又起而危及政權,因此在遷臺後,便對校園展開嚴密的掌控,透過軟硬兼施的手段來掌握校園內的學生活動。
在那段時期,校方不僅用非常時期法令來限制學生活動,也成立黨社以監控社團,藉此建構嚴密的掌控系統;在學生自治方面也培養由救國團主導的自治幹部,限制學生自治的發展,持續削弱學生自主思考的可能性。野百合學運學生領袖范雲接受採訪提及當時自己剛進臺大時的心得:「在我的想象中,臺大裡面應該是很多對社會有熱忱、很有人文氣質的人,但進入臺大之後,發現大多數人都在聯誼烤肉,所以有點失望。」
相較於今日開放多元的校園,當時政治、社會議題並非能夠那麼自由、廣泛地被討論,使學生要接觸乃至加入相關議題社團會有所顧忌,才造成了大多數人只參與聯誼性活動的現象;然而,這並不代表校內便是一片死寂,依然有著部份學生透過自行組織或是社團的形式,在校內進行社會議題的倡議,讓民主思想在校內有了萌芽的機會。
民主萌芽:校內社團與學生活動
當時的大學新聞社、大學論壇社、大陸問題研究社為當時臺大三大社,這些關心社會議題的社團在當時被稱為「異議型社團」,野百合學運中不少人都曾參與其中,這些社團也站在校園民主改革的第一線。當時學生們在校園中推動校園言論自由,在傅鐘前舉辦演說,互相辯論思想。而三大社之後,也出現了九大、擴張到十三大,越來越多的社團成立,例如環保社、女研社、濁水溪社與臺灣研究社等等。范雲描述這些社團的關係時提到:「這些社團既合作又衝突,維持互相監督的關係,彼此之間透過不斷的溝通來達成共識。」
1986年,大新社(大學新聞社)將刊物送給校方審閱,卻被校方認定違反評閱辦法,強制停止社團一年,以及懲處相關人士。此舉引起臺大改革派學生的抗議,在校門口舉辦惜別會,同時也發行地下刊物《自由之愛》。值得一提的是,過去只有少數人的抗爭,卻因自由之愛事件引起了其他學生的關注,使改革派的思想漸漸在校園內受到認同,也讓改革派於隔年的代聯會選舉中大獲全勝。
在自由之愛事件之後的時期,改革派學生除了在臺大校內進行倡議,也與其他校學校的類似社團有所連結。當時為臺大傳真社社員的周克任,就曾聽聞過臺大與他校改革性社團的關係:「彼此都會有一定程度的互動交流,甚至合作辦理特定議題的培訓營隊;但在爭取《大學法》的運動中,曾經與他校種下一些『不愉快』的火苗。」不過他也提到,各校之間的衝突,其實往往不是基於立場或意識形態下的分歧,只是往往會用此來當作說詞:「說穿了其實都是誰動員、誰指揮這種爭權問題。」

在校園之外,社團也與其他組織合作,主要是社會運動組織,例如環保聯盟、勞動團體等等。范雲舉例:「當時的女研社與婦女新知關係不錯,是因為透過在組織中擔任志工有所連結;像大陸社就比較多是和編輯黨外雜誌的學長姐合作,偏向個人關係。」至於當時成立不久的民進黨,當時並不方便公然進入校園,因此多為檯面下非正式的協助,間接地提供學生運動在器材方面的支持與協助,例如借發電機、音響戰車等。透過這些人脈的連結,學生從這些校外組織得到了不少幫助,而非只是憑藉自身力量孤軍奮戰。
改革派學生們主動地在校內推行民主與學生自治的發展,而各個社團也將社會中各項議題的討論帶進校園,逐漸為校園內帶來新的氣象,並撐起了校園民主萌芽的空間。這種輻射性的擴散,雖然在當下看起來沒有明顯成效,擔任倡議角色的學生群並沒有進一步擴大;然而,就在八零年代末期,社會上針對國會改革的聲浪逐漸加劇之際,校園中累積的民主意識與政治參與能量彙集,成為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不過,在跨校合作的過程當中,曾累積下來的不愉快經驗,也為後續學運的溝通過程埋下衝突的可能。
天時地利人和:野百合爆發前夕
國會改革的議題,其實早在國大代表宣布延長任期前,就已獲得當時臺大學生會的注意:「那時寒假結束後我們決定要做國會全面改革的議題……我們舉辦演講,展開動員,像是有個臺大學生給老國大的一人一封信等等。」當時擔任學生會長的范雲表示,這個議題對於其他社團的吸引力比較低,跟校園民主的距離也比較遠,所以他們決定自己來做。
九零年的三月恰逢總統大選,而在蔣經國過世後,國民黨內部產生了派系的鬥爭,此次選舉分出了主流派李登輝、李元簇與非主流派的林洋港、蔣緯國兩組人馬競爭,而當中又牽涉省籍問題,引發社會的動盪不安。臺大學生會針對此事開會討論,最後決定將倡議的焦點放在並無民意基礎的總統選舉,主張先停止這次的選舉並改革憲法後才由人民選出國家總統,並規畫要在國民黨中常會當天進行抗議;然而,同年3月9日,非主流派候選人宣布退選,社會恢復穩定,再加上群眾相信李登輝會進行改革帶來新氣象,許多原先參與的團體、教授因而打算退出行動,以求社會安定。臺大學生則認為在制度上,由國代選出總統缺乏民意基礎的問題仍未改變,因此堅持原定的抗議計畫,在3月14日前往國民黨黨部靜坐抗議,這個決定也是影響未來野百合學運發展的重要轉折點。
剛好在抗議的同一天,老國大突然宣布延長任期、為自己加薪。此舉引起社會強烈的反彈,不僅是在野的民進黨,甚至國民黨也動員各議員到省議會抗議,此次的靜坐抗議也意外的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范雲提到當時抗議的場景:「當時他們在陽明山上開會,我們在山下抗議,剛好就擴大報導到我們,其中也有很多可供報導的素材,如:學生與鎮暴警察追逐的畫面,就很有力量。」在14日抗爭結束之後,學生聚集繼續討論運動延續的可能性,召開了3月16日早上的會議商討,想不到在當天,卻有意想不到的變局……
學運的爆發 學生的集結
「同胞們!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
1990年3月16號下午,臺灣大學學生會還未討論出結果時,就讀大氣系二年級的周克任便與八名同學攜標語進入中正紀念堂靜坐,對於國民大會修正《動員戡亂臨時期條款》,擅自擴權,表達抗議,揭開「野百合學運」(也稱「三月學運」)序幕。
「當時並沒有一大群人講好大家一起做些什麼,就只是大家剛好都一起行動了,真正發展成後來六天的大規模活動,是因為社團與校園自治組織講好,大家一起去。」與周克任同為傳真社社員的洪貞玲表示,野百合的爆發是一種偶然,因為這場學運的爆發並非是組織好的行動;但它卻也是一種必然,因為當時社會對民主化的訴求,對於萬年國代的不滿已經醞釀到一定程度,勢必會有一場大的爆發。
靜坐的第一個夜晚,學生人數與媒體的注意都不多,但是,消息已經透過學生間的網絡傳開,響應學生先後進入中正紀念堂,現場從寥寥數人擴至百人以上規模,同時,關心此次運動的民眾也漸漸聚集。隨著參加人數越發增加,眾人分別隸屬不同學校、不同社團組織,恐有意見分歧的隱憂,為了維持整體秩序,明確運動方向及訴求,各校決議成立「七人決策小組」指揮現場,包括范雲、周克任等。雖然學運有了領導組織,但彼此之間仍有自身定位差異,這是由於在校內倡議性活動扮演的角色、經驗不同造成。
 近6000名來自台灣各大學院校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
近6000名來自台灣各大學院校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
周克任作為最早行動者,認為:「學生沒有走出來是無法改變歷史的。」因此攜標語偕同夥伴前往中正紀念堂靜坐。他希望作為起頭者,能成為突破口,鼓勵更多的學生,不過卻也是抱持著破釜沉舟的心態:「其實我們並沒有預設會有更多學生參加,反而是自認大概行動當晚就會被抓走,然後可能不知失蹤到何方去了。」至於是否期待藉此進入決策核心,他認為自身對政治的理解不深,在校園改革性社團也非領導角色,故並非因抱持著這樣的想法才行動。
當時臺大的組織與社團並沒有率先參與,反倒是中興法商等校的學生團體先來,由於彼此不熟,最初僅是彼此觀察試探:「他們大概是想知道我們是不是真的是臺大改革派的系統,還是只是假動作,或根本是國民黨學生來挖坑給大家跳。」周克任推測,彼此除了安排靜坐空間以外,只有交換意見,還未有聯盟性質的決策組織。
臺大學生會在14日的抗議行動後,與傾向改革的大學彼此聯繫,才決定將行動延續,於是規劃在3月18日進行學生大集結,直到這時,周克任與較早加入靜坐的學生,才與各校串聯動員的學生合併,整場運動的人數到達新高點,原本僅一日的集會,順勢發展為多天的連續活動,正式的決策系統也在此時組織。
野百合學運的爆發,並非是在全體具有共識的情況下發生,進入廣場們的學生們雖懷抱著同樣的理念,向政府爭取共同訴求,但在組織、手段或方向上仍有一定差異。在這樣的情況下,參與運動的學生們必然出現意見上的分歧,而這樣的分歧也時刻牽動著運動的發展。
野百合學運間的分歧
3月18日,各校學生於中正紀念堂會師後,現場人數超過3000人,野百合學運進入高潮,校際會議代表學生們正式提出「四大訴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政經改革間表,要求當局回應。

這一天是學運對外的重要時刻,對內也是如此:決策委員會(即「決策小組」)擴充人數、接納各校代表,改名「校際會議」,確保決策的周延與代表性。
隔天,校際會議決定以「野百合」作為本次學運的象徵,寄託自主性、草根性、生命力強、春天盛開、純潔以及崇高的精神。時值總統大選前一日,總統府以新聞稿正面回應學生訴求,李登輝已決定召開國是會議。同時,決策小組再一次改組,以各校改革派社團代表為主,賀德芬、瞿海源等教授也進入決策。現場人數不斷增加,意見不合的情況越發頻繁,決策小組與一般學生摩擦不斷:「我們是由各校的進步社團組成,臺大與各校都有一定的席次,決定了現場要有決策小組,但在場內決策小組承受極大壓力,不得不擴大。因為有不同方的代表,於是擴大編制。」范雲如此描述當時擴大決策圈的考量。
同時,民進黨人士參與,教官以及國民黨學生社團也出現在廣場上,甚至教育部長李煥都前來探視,引起決策學生不安。現場人員眾多、龍蛇雜混的情況下,難保不會混入有心人士,在學生間製造事端,藉此污名學運;或者政治人物涉入,使「學生運動」性質不再單純,玷汙野百合純潔的寓意。決策中心面對大量衝突、龐雜現場的巨大壓力,為了減輕負擔,提升討論效率,讓廣場學生獲得更多參與權力,討論決策的重心從校際代表會議轉移至各校內部。
3月21日中華民國第八任正副總統選舉結果公布,由李登輝、李元簇當選,李登輝於當日下午即接見學生代表,答覆學生的訴求。「大致而言,李登輝給予的答覆是善意,但不是非常明確;也有學生和社團認為集結不易,應當採取更強勢的行動,對政府再次施壓。」周克任認為,對於沒有大型群眾經驗的學生而言,要在有限時間內處理廣場學生們的意見本來就很困難,加上缺乏情資網路幫助判斷,自然會萌生「見好就收」的念頭。
不僅如此,參與學生規模增加以及來源陌生,變動風險也隨之增加,紛亂的意見使得討論冗長耗時,疲憊恐影響決策者判斷,更增加不確定性。在內外種種不利因素下,既然訴求已經取得階段結果,而決策的責任在周克任看來又過於沉重:「誰也不願意擔上「冒進」的歷史責任,且一旦發生不可預測之衝突,『求穩定中改革』的社會輿論,恐怕不會跟學生站在同一陣線。」周克任表示,最後退場決議由各校內部討論表決後,交付校際代表至校際會議提出,一校一票表決,而決策小組只擔任執行決議之角色。
根據最終表決結果,學生於22日早晨退出廣場,野百合學運和平落幕;然而,在這短短一週內,便可看見學運中充滿各式各樣不同的理念和聲音:決策學生不同的自身定位、決策學生與廣場學生意見相左、教授的作法與學生的反彈、退場決定……等等。在下一篇中,我們將觀察這些分歧如何產生與被調和,藉以理解學運過程中的權力流動,而這同時也是影響這些人民主參與經驗的一個深刻印記。
※作者為臺大學生會新聞部成員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2025 端午節】全台 12 家人氣冰粽推薦!星巴克、義美、85度C、元祖、紅豆食府都有 乖乖竟然也出粽子
- 劉宇寧、宋祖兒《折腰》2大敗筆Netflix收視下滑 慘輸秦漢與謝盈萱新劇《忘了我記得》
- 【內幕】輕巡艦量產計劃縮水 減少5艘改2500噸雙船體火力艦
- 《藏海傳》爆紅肖戰接演《知否》導演諜報新劇 搭檔《愛情而已》的「她」遭粉絲抵制
- 《折腰》宋祖兒主動吻上劉宇寧全網暴動 她躺床撒嬌喊「這句話」全網甜暈
- 楊冪新劇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趙又廷合作破局 改搭《難哄》的「他」被酸資源降級
- 《藏海傳》肖戰演技超越舊作《慶餘年》獲好評 劇情卻因2大敗筆慘遭吐槽
- 《折腰》劉宇寧與宋祖兒圓房名場面搶先曝光 兩人床上吻到喘息性張力大噴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