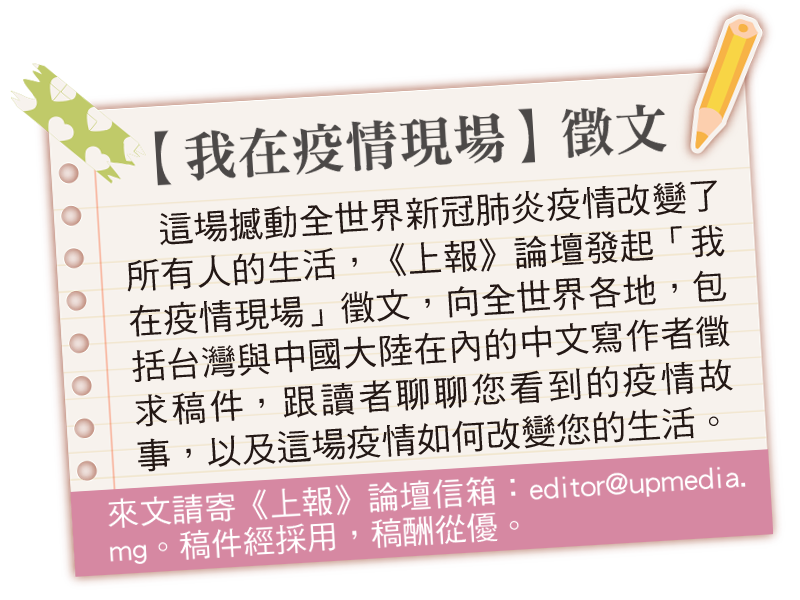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王鴻薇爆郭智輝曾違反證交法遭判緩刑 更助中國設立晶圓廠 2024-04-16 17:50
- 最新消息 前委員蕭祈宏涉任詐騙集團顧問被起訴 NCC遺憾:打詐勿枉勿縱 2024-04-16 17:32
- 最新消息 《淚之女王》金智媛、金秀賢相戀又甜又虐超催淚 她曾對「這位男神」動心內幕曝光 2024-04-16 17:30
- 最新消息 【有片】習近平見蕭茲:中國出口電動車等產品有助緩解全球通膨 2024-04-16 17:25
- 最新消息 唐鳳無緣續任!進入政壇8年 從「天才IT大臣」到爭議不斷 2024-04-16 17:25
- 最新消息 自爆其他陣營頻招手卻落腳基隆 楊寶楨嘆:政治圈有太多肅殺 2024-04-16 17:00
- 最新消息 羅雲熙新劇18套造型曝光超吸睛 黃金戰甲上身霸氣超越《長月燼明》 2024-04-16 16:50
- 最新消息 黃曙光向蔡英文請辭國安會諮委、潛艦小組召集人 黃珊珊證實 2024-04-16 16:50
- 最新消息 個人形象爭議太大 川普封口費案審判首日選不出陪審團 2024-04-16 16:36
- 最新消息 永慶房屋贊助113年全中運賽事 台北市政府頒贈感謝狀 2024-04-16 16:25

今年是韓國光州事件四十周年,受難者靈魂的目力所及,不再是縱橫交錯的人塔,而是肅穆安寧的公園。(維基百科)
今年是五·一八光州事件四十周年,筆者重讀萬海文學獎獲獎作品《少年來了》,作者對少年命運的記述,對暴力與人性的探討,對人性邪惡與善良的刻畫,穿越卌載,依然具有深刻的衝擊力。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獨裁者朴正熙被親信金載圭槍殺,國務總理崔圭夏以總理身份代行總統職權,十二月六日繼任總統。崔圭夏按照美國意圖廢除了朴正熙的第九號緊急命令,釋放了部分政治犯,獨裁統治得以放鬆,韓國出現了短暫的「漢城之春」。十二月十二日,陸軍少將全斗煥以調查朴正熙遇刺案為由發動肅軍政變,政變成功後掌控了軍權。受美國壓力,全斗煥被迫承諾軍方不幹預政治。
與此同時,韓國爆發了反獨裁的學生運動,規模不斷擴大。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日,全斗煥拋棄不干政的承諾,頒布了非常戒嚴令,宣布停止一切政治活動,關閉了所有大專院校,大舉逮捕學生領袖和政治犯。五月十八日至五月二十七日的十天,光州市爆發了大規模反對戒嚴令和獨裁政府的示威並一度控制了整個城市,全斗煥調動數萬名軍警鎮壓示威群眾,致使近千人喪生、上萬人受傷。光州事件後,全斗煥從文官手中奪取了政權。
《少年來了》以此為背景,回溯彈壓前一刻主人公的心路歷程,也記述事件卅載後的漫長遺緒,作者基於扎實的采訪將自己對光州事件的感受與疑惑熔鑄在六個人物故事中,包括協力整理屍體的國中生姜東浩,東浩已故的好友正戴,被警察掌摑的出版社編輯金恩淑,被逮捕的示威者金振秀,被凌虐的女工林善珠以及失去兒子的東浩母親。小說的六個章節各自著眼於一個不同的角色和角色的心聲,六個聲音串在一起構成了光州挽歌。透過互相鉤連又獨立於世的人物命運,作品還原了光州十日裡親歷者的悲劇,也反映不同時空中暴力之上的人性。

敘述人稱與詩意語言
《少年來了》以東浩的故事為主線,透過其他角色對東浩的回憶串聯起整個故事:國中生東浩和朋友正戴一起參加了示威,戒嚴軍入城屠殺時,東浩逃過一劫,卻目睹正戴被當街射殺。東浩來道廳的尚武館找尋正戴屍體之際先後遇到恩淑、善珠和振秀。軍方即將攻入道廳的那晚,東浩下定決心要堅守到最後,道廳外的東浩母親無法進入勸說,為避免更大的損失拉著另一個孩子回家,三十年後依舊懷抱愧疚。被逮捕的振秀在拘留所遭到嚴酷拷問,出獄後痛苦與自責仍讓他無法釋懷,最終選擇自殺;五年後成為出版社編輯的恩淑無法忍受在烤盤上慢慢烤熟的生肉,這讓她聯想到那一晚在道廳協力處理過的屍體;二十二年後,面對尹教授對光州事件采訪調查,善珠思緒萬千、遲遲無法開口……
死者已矣,倖存者的餘生也被釘在了那一晚,愧疚與痛楚仿佛夢魘般在不經意間浮現。小說重點展示的正是生者對死者懷抱的情緒,「他們代替我們犧牲了寶貴的生命,而我卻還活著」。其中不時出現的第二人稱敘事凸顯了故事的在場性,對於增強作品的感染力意義重大。
文中的「你」承擔了雙重角色,既是第一章裡的「角色」國中生東浩,也是正在閱讀東浩故事的「讀者」,第二人稱讓故事仿佛在當下生成,當敘述人稱為「你」的時候,讀者會不自覺地進入文本世界,把自己置身於東浩的位罝,這時讀者不再是置身事外的觀察者,而是堅守道廳的當事人,展卷之際和角色同悲同喜,給讀者以「這就是我的體驗」的感覺,以引起不同讀者與作者的共鳴,當讀完這部作品的時候,每位讀者都會有自己心中的「少年」。
第二章裡,作者塑造被軍隊殺害並焚屍滅跡的正戴時,則用靈魂出竅的方式刻畫軍隊鎮壓的殘酷,「第一座推成人塔的那些軀體最先開始腐爛,上頭爬滿了白色的幼蛆。我默默地看著我的臉一塊一塊的腐蝕,五官已經變得模糊不清,輪廓也不再清晰可見,任何人再也辨別不出那個人是我。」
作者韓江九〇年代初入文壇便選擇詩歌作為主要的創作體裁,之後才轉戰小說,或許正是這一經歷,韓江的小說像詩一樣精巧綿密,詩意在小說中將其透過臺詞、心聲、夢境等形式表現出來,使抒情充滿張力,敘事充滿力量和深度。小說藉著人物之口對讀者發問,「那麼,我們該思考的問題是:人類究竟是什麼?為了讓人類不要成為什麼,我們又該做些什麼?」隨著情節的展開,這個問題的矛盾和答案變得更加鮮明。
失去你們之後,我們的時間變成了黑夜。
我們的家、我們的街道變成了黑夜。
我們在越來越黑,再也不會明亮起來的夜裡吃飯,走路,睡覺。
我無法為你舉行葬禮,從此我的人生變成了一場葬禮
在你死後,我沒能為你舉行葬禮
導致我那雙看見你的眼睛成了寺院
我那雙聽見你聲音的耳朵成了寺院
我那顆吸著你氣息的肺也成了寺院
春天盛開的花朵、柳樹、雨滴和雪花,都成了寺院
日復一日的黑夜與白天,也都成了寺院
就在你被防水布包裹、被垃圾車載走以後
在無法原諒的的水柱從噴水池裡躍然而出之後
到處都亮起了寺院燈火
在春天盛開的花朵裡
在雪花裡
在日復一日的黑夜裡
在那些你用飲料空瓶插著蠟燭的火苗裡
 光州事件發生地點:全羅南道廳舊址及前方的錦南路。(維基百科)
光州事件發生地點:全羅南道廳舊址及前方的錦南路。(維基百科)
暴力之上的人性
和前作《素食者》一樣,韓江的《少年來了》英譯本由Deborah Smith譯成英文,不同的是,譯者反復比較推求後,英譯書名沒有選擇直譯的The boy is coming而是有些抽象的Human Acts。譯者本人解釋,第一個理由是這部小說探究的不是暴力而是人性,溫柔或暴力、勇敢或怯懦的「行為」都是人性的表現。其次,Act也指(戲劇中的)「一幕」,這和六個人物、六個故事的結構方式相應,也暗指第三章裡那場隱喻般的無聲戲劇。
韓江於一九七〇年生於光州,九歲時舉家搬至首爾,逢年過節時總會看見長輩們刻意壓低聲音交談。踏上寫作之路後,韓江不斷思考自己為何總對人性保持懷疑,終究發覺一切皆來自這件無法全盤理解的殘酷事件,因此,她決定以自己的方式提筆寫下,這本書也是作者對自己缺席與盲點的一次補正。
在第三章《七記耳光》中,作者藉由被檢閱組刪減的劇本臺詞向讀者發問,「人類究竟是什麼?為了讓人類不要成為什麼,我們又該做些什麼?」國家暴力殘酷和人性細微處的善良在充滿了感性和知覺的細節描寫和心理描寫裡體現得淋漓盡致。
光州事件裡,戒嚴軍拿到八十萬顆子彈,而當時光州人口也不過四十萬,這意味著足夠把每位市民射殺兩次,「就算是醫院裡的傷患也都是叛徒,統統得槍斃」。而留守道廳、以良心和軍隊對抗的少年們拿著從預備軍訓練所來的槍防衛,「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他們(軍隊)就會把我們趕盡殺絕」,拿到搶的少年們卻不忍心去使用,因為他們無法做到對一個活生生的人扣下扳機,讓鮮活的生命變成他們曾整理過的屍體。
此外,戒嚴軍的罪責不僅有殺害,還有凌虐。在尾聲《雪花覆蓋的燭燈》中,作者以自己的口吻寫道,「初次接觸資料時,使我最不解的部分就是軍人不打算進行逮捕,而且一再殺戮,光天化日之下,毫無罪惡感,毫不遲疑的凌虐施暴,此外還有那些下令盡可能殘忍行事的指揮官。」
這種殘忍的凌虐在第五章《夜空中的瞳孔》借由善珠的回憶體現得十分典型。被捕的善珠過去從事過工會活動被扣上「赤婊子」的帽子,遭軍人虐待,劫後,記憶稱為她揮之不去的夢魘,即便度過二十二個春秋,面對尹教授涉及光州事件女性角色的調查采訪,她依舊難以啟齒。
有人拿一把三十公分的木尺不斷往妳的子宮裡來回鑽數十次,說得出口嗎?有人用步槍的槍托肆意妄為地撐開妳的子宮入口,說得出口嗎?他們將下半身一直血流不止導致昏厥的妳,帶去國軍總醫院接受輸血,說得出口嗎?下體出血持續了兩年時間,血凝塊堵塞輸卵管使醫生宣告妳終身不孕,說得出口嗎?妳已經再也難以和其他人——尤其是和男人有所接觸,說的出口嗎?包括簡單的親吻、撫摸臉龐,甚至是夏天露出手臂和小腿時,他人停留在妳身上的視線,都會使妳感到痛苦難耐,說的出口嗎?妳開始厭惡自己的身體,摧毀所有溫暖與愛意並逃離現場,把自己封閉起來,說的出口嗎?逃到更冷更安全的地方只為存活下去。
戒嚴軍中也有沒那麼好勇鬥狠的軍人,在外國記者鏡頭捕捉的畫面中,有軍人會在受命向市民射擊時故意射偏,有軍人把受傷市民背到醫院門外倉皇離開,有的在道廳一排排的屍體前列隊時閉口拒唱國歌。對於殞身不恤的少年們,作者也沒有作拔高的描述,正如振秀的獄友回答的「有人被群眾的熱血感染而勇氣十足,但事後回想起守城的那一夜,自己當時真的沒有那種必死的決心。」
今日的光州街頭,悲情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積極進取的氛圍,正如第六章《往花開的地方》裡東浩母親回憶起東浩兒時的故事,母子牽著手沿著河川的街道去店裡找東浩的父親,活潑的東浩用力拉起母親的手把她拽到有陽光的地方,「媽媽,那邊有陽光的地方還開了好多花,為什麼要走暗暗的地方,往那邊走,往那花開的地方。」受難者家屬的傷痛終有一日能夠愈合,受難者靈魂的目力所及,也不再是縱橫交錯的人塔,而是肅穆安寧的公園,讀者也能夠帶著少年的故事,迎接另一段開始。
※作者為中國大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