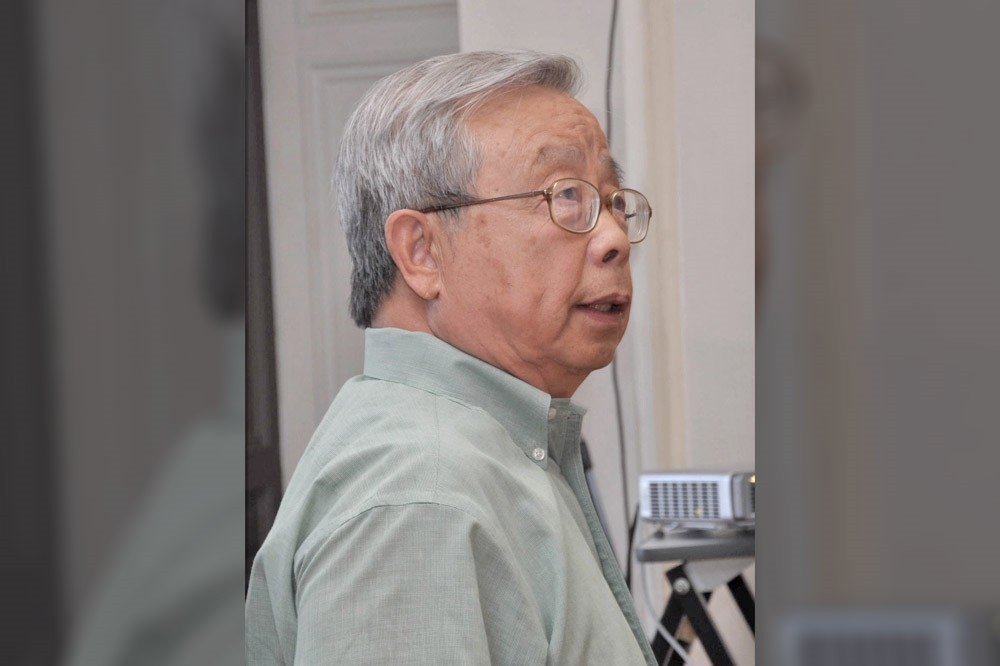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榛果樹」飛彈明年到 白俄總統:已佈署數十枚俄羅斯核彈 2024-12-11 18:20
- 最新消息 張若昀《慶餘年》第二季流量奪冠成劇王 他開2千萬跑車因「這舉動」形象全毀 2024-12-11 18:01
- 最新消息 賴清德分享出訪友邦3大收穫 強調「民主台灣絕不走回頭路」 2024-12-11 17:54
- 最新消息 尹錫悅總統辦公室阻擋警方搜查 雙方僵持6小時仍在對峙中 2024-12-11 17:43
- 最新消息 陳妍希父親過世陳曉沒出聲被罵翻 他被拍到爛醉「需旁人攙扶」畫面曝光 2024-12-11 17:27
- 最新消息 國泰金展望2025經濟 川普2.0之下明年Q1「晴朗轉陰」 2024-12-11 17:22
- 最新消息 【大法官人事案】逾8成民意不滿實質廢死 陳運財:憲法法庭不受民意拘束 2024-12-11 17:22
- 最新消息 「一隻阿圓」穩交陳百祥 眼尖網友:去年就曾一起去韓國! 2024-12-11 17:20
- 最新消息 中國對台野心變本加厲 陸委會:雙城論壇應避免成為政治宣傳工具 2024-12-11 17:20
- 最新消息 日本人氣超商LAWSON有望來台?悄悄註冊2商標 網友樂喊:想吃炸雞君 2024-12-11 17: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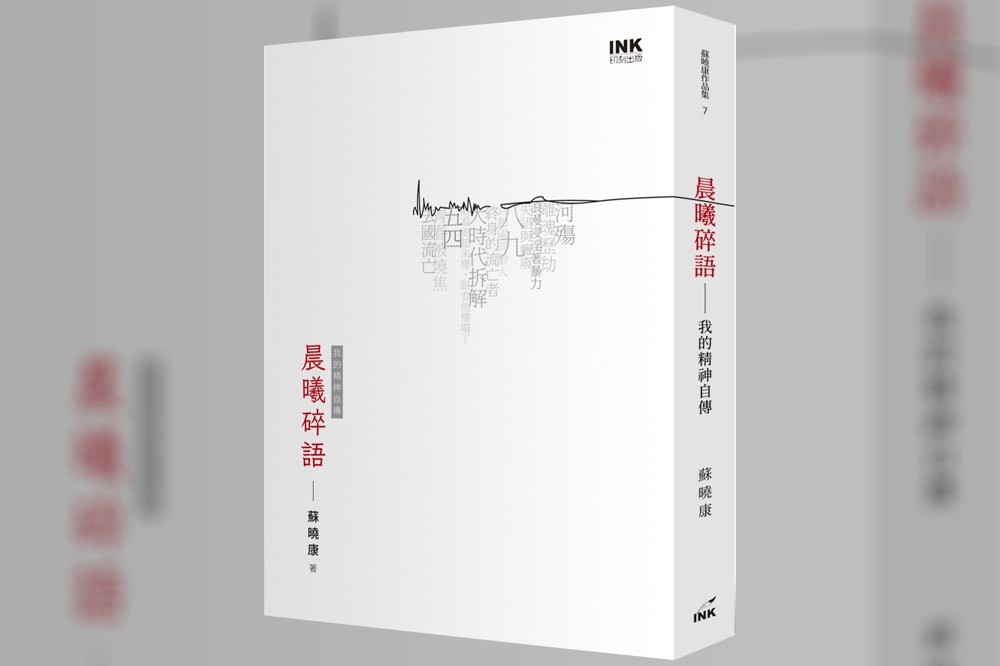
《晨曦碎語──我的精神自傳》書封。
我朦朧記得:當初我倆在巴黎聖母院一道跪下去的時候,你兩肩劇顫,在那穹窿下久久匍匐,不能起身;我雖也動容,卻有些勉強。五年後我才悟到,那一瞬間對你我的意義竟在霄壤之別,以致今天我自覺沒有資格同你議論spiritual,所謂超越世俗的、神界的事。我越來越覺得有一道天塹,橫在現實世界與超越世界之間。你我彷彿都未覺察到的一個基本困難,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我聽不懂你所說的,你似乎也難隨著我沉淪到一個世俗人的絕望、無助和掙扎中來。
五年前的那一瞬間,我還在逃亡後的虛脫中,思緒紊亂,到神靈面前能揀出來的唯一祈求,是懇請上蒼護佑我的妻兒。我的虔誠已在青少年時代揮霍殆盡,那祈求只是倏忽鑄成流亡命運下投向神靈的一縷私願,一如中國人常說的「臨時抱佛腳」。是不是那一瞬間的輕率,便注定了我對流亡的殘酷程度,和日後還將遭遇的厄運,竟然渾然不覺,以致讓我的妻子千辛萬苦牽著兒子奔來美國,打工熬日,伴我流亡,竟還要被一場車禍撞成癱瘓?我不知道。只知道那一瞬間如今化成一個揮之不去的內疚,時時折磨我。更深的創傷還不是這些,而是在我伴她慢慢從地獄走回來的一年多裡,目睹一個身心俱毀、記憶消失、時空破碎的人是怎樣被「修復」的。我經歷了一次人的毀滅。
有個清晨,她仍昏迷在急診室裡,我一個人恍惚出去,站到靜寂的高速公路旁,只有一個了結的念頭在翻騰。當時閃過的念頭,後來我從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一段文字裡又讀出來:「……希望永遠失去了,而生命卻單單地留下,而且,在前面尚有漫長的生命之路要走。你不能死,即使你不喜歡生。」我在日記裡寫道:「這是近十個月來我所讀到的最貼近我心境的文字,從未有過的絕望而又不能被安慰也無法被替代被宣洩的感受,以及人生曾獲得的一切,消失得無影無蹤,讓你抓不到一根救命稻草,這些大概就是我一生沒有意識到的個體靈魂中最隱祕的無根基性。」人在多大程度上能主宰自己的命運,此時對我已成一種滑稽。我的意思是,我們曾是那樣自信於「修復」國家、民族、社會、文明之病入膏肓的一類「人物」,臨到獨自面對一個人和一個家庭的災難境地,除了天塌地陷之感,一無所憑。我忽然看到了存在的深淵,一個無底的黑洞張開在腳下。
在這個懸崖上,此岸的現實世界彷彿只給我留下了求生的本能,和一個要救她的瘋狂念頭,同這念頭相連的,就是對人世之外的奇蹟的渴望,它拚命飛向了彼岸,那個對我來說陌生卻從不想去觸碰的神祕世界。車禍後來自基督教、佛教和氣功對我們的救助,也是源源不斷,我要自己絕不拒絕來自彼岸的任何救助,各種禱告、默想、入靜我也一一都做了,只為她默默去做,不因我而成為一個障礙。我知道這不是信仰衝動的發生,只是一個世俗人的絕望而已,如果這個絕望發生在五年前的巴黎聖母院裡,又當別論。眼下,我所渴望的只是神蹟的降臨,這成了一個極功利的判斷,它在此岸和彼岸之間築起一道屏障,叫我逾越不了,終因未見有奇蹟降臨於我們,使我不能擺脫塵世。
然而,事情並非如此簡單。一九九三年的寒冬,在美國東岸是數十年來未有的冰雪交加。每天清晨我砸開裹在汽車上的一層冰盔甲,趕到醫院去會我那神志混沌的妻子,聽她訴說種種非人的夢境,和時空破碎之中溢出的囈語,還要狠心逼她作各種鍛鍊,不覺夜幕落下我非離去時,總要聽她喃喃道:「這一夜怎麼熬呢?」外面雨雪霏霏,我上路去,車裡會響起一盤磁帶,是過去她哄兒子入睡時常哼的兒歌,她昏迷時我又不斷在她耳邊放過,此時會叫我聽得淚水迷濛,看不清高速公路。回家給兒子弄了晚飯後,一沾床淒涼難忍,不由自主會跪到一個木製的基督受難像前,求神去驅趕她的惡夢,求神帶我去陪她,這樣做了之後我竟夜夜一覺到天亮。但久而久之,我發現所做的這一切都是在寬慰我自己。其實對奇蹟渴求最劇烈的,是我那惶亂如在無底深淵的內心,它於禱告的一瞬間有了著落。
人之心底,真有一個自己也未曾相識的靈物,我在災難中同他相遇。這個內在的靈物,不受意志或觀念、理性等的控制,自有他一套神祕的調理機制,他的悲痛是你無法壓抑的,而他的節制也是你意識不到的。車禍一年多後我在日記裡寫道:「已自覺開始平靜下來,昨天同醫生談話時曾突然傷感了一下,此後再無哭的衝動,只在驅車途中聽那憂傷的旋律時尚有舔傷口的痛感。人的心情真是奇妙,我對『他』的陌生真是一個四十年的漫長故事,卻在今天才意識到。如此說來,她的那個『她』又該何等神祕和陌生。」人尚且不能認識自己內心的這個靈物,何談他者?思想家們對所謂理性和非理性的探尋,以及其中的誤差,大概都導源於此。宗教的所謂「屬靈」是否指此?
我的確還不清楚。我的感覺可以告訴我,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裡有所謂spirit,或悲或喜,或善或惡,僅憑世俗的經驗和意志去控制,非常有限。一旦與神界溝通,連接了超越性的境界和力量,人的精神可以越過肉身、經驗和世俗,獲得提升。然而,神界在哪裡?對於還沒有信仰的人來說,尋找似乎又只能依賴自身的內在靈物,即所謂靈性,有的人可以一點就通,有的人如我,就是愚不可及,只要尋找一開始,經驗、理性都跟著復活,恰恰是南轅北轍。我的困境更在於,我根本不認識自己內心的那個「非我」。也許,人生的另一番境界,就是同自己內在的這個靈物溝通,隨從他去超凡脫塵,褪卻肉胎。
一位傳教者有次對我說,跨越人間的唯一路徑是「死」一次,意即「重生」一次。肉身之死的慘烈,這次我妻子領教了。她在一剎那間就喪失了人體的一切基本功能,僅存一絲遊魂在陰陽界飄蕩。人世對她已成一個幻覺,她不知道自己在哪裡,這個世界除了兒子都是陌生人,甚至連我究竟是誰也模糊了。這大概就是所謂「靈魂出竅」,肉體已成一軀殼。混沌中,她說她有一次遇到了神,在大海上,有一個很高的聲音在說話。這樣的事她只說過一次。我自己的崩潰感,則只在人生的枯竭和幻滅上打轉,覺出往日如浮雲瞬間渺不可尋,自身只如赤條條一個皮囊而已,也作了種種呼號和求告的努力,卻同那神或佛都無緣接通。這次大難雖將我們置於塵世的懸崖,但我們的精神卻只在懸崖上徘徊。人被毀滅的滋味嘗到了,卻並未因此而「重生」,於是,我們只是有了一次地獄之行。
車禍後有位前輩學人來看我,沒說多少寬慰話,只說:列夫.托爾斯泰說過,人受難時要想一想自己有沒有資格承受。當時我並沒有聽懂其中的意思,後來才慢慢嚼出味道……
一九九五年一月四日
※本文摘自《晨曦碎語──我的精神自傳》(印刻文學出版,蘇曉康著。本文為1989年蘇曉康出逃香港,回應「六四」近兩萬字專訪,首次完整揭露。評析趙紫陽、胡耀邦、李鵬,悼方勵之、劉賓雁,解讀劉曉波、高行健、廖亦武、王丹、柴玲;追蹤「五四」胡適、梁實秋、知堂;描摹余英時與海外飄泊學人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