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全台再降溫!明起又濕又冷下探10°C 「這天」有機會下雪 2024-12-13 10:20
- 最新消息 美前國安顧問歐布萊恩證實替賴總統轉交賀函 稱川普收到之後很開心 2024-12-13 10:01
- 最新消息 叢林探險!《潛水員戴夫》宣布 2025 年推出 DLC《In the Jungle》 2024-12-13 09:53
- 最新消息 拜登宣布特赦39人、替近1500人減刑 創下美總統近代單日最高紀錄 2024-12-13 09:52
- 最新消息 【有片】9艘中國海警船凌晨逼近我國海域 海巡「1對1緊盯防守」畫面曝光 2024-12-13 09:49
- 最新消息 黑夜君臨!《艾爾登法環》宣布 2025 年推出多人合作類衍生新作《Elden Ring Night Reign》 2024-12-13 09:25
- 最新消息 黑熊學院遭爆使用中國製空拍機 還被抓包清除「原始數據」 2024-12-13 09:24
- 最新消息 北約秘書長呂特呼籲認清北京野心 直指「中國正在霸凌台灣」 2024-12-13 09:17
- 最新消息 華府政策轉向? 川普批評烏克蘭用美國飛彈攻擊俄羅斯領土「太瘋狂」 2024-12-13 08:51
- 最新消息 千呼萬幻等到你!《PTCG Pocket》12/17 推出「幻遊島」 夢幻ex、時拉比ex 登場 2024-12-13 08:41

中共當時加入聯合國不久,把美國的毛派反帝年輕學者請來參訪,是個重要的統戰任務。(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左)和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右)。圖片取自網路)
1973年美國毛派「關切亞洲(研究)學者委員會」(CCAS)初次抵達中國大陸訪問。他們寫過許多文章,也在討論會中讚揚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人道的革命社會。
毛派出發之前,曾經有過一段冗長的內部辯論,討論為何而去,應該讓誰去,以什麼身份去(學院的學者還是中國的友人?)等問題。而中共內部也為這次大魚上鉤的統戰任務,做了周詳的準備。結果,這些別著自製的「打倒美帝國主義」飾牌的「關切學者」,行程安排緊湊,排定了一連串的參觀節目。中共的意圖是寄希望於美國下一代的年輕人。
參訪結束時,招待宴會的最後一道菜是一條大魚,廚師把魚眼挖掉,在魚眼處裝上兩個閃亮發光的小燈泡,雖然怪異,但也不能不佩服廚師的匠心獨具。
CCAS的一名團員 在舉杯答謝時,忍不住調侃了一句,感謝中國主人的盛情招待,最後還讓他們見識到一條眼睛有毛主席思想發電的大魚。那天晚上,中共幹部要這些關切學者在旅館裡做檢討和自我批評,為他們褻瀆毛澤東思想贖罪。這些天真的「關切學者」何嘗瞭解,他們到達中國的時間正是拜毛教的頂峰時期。若是換了一般中國人,這樣一句玩笑話就是大逆不道,足可投獄經年,不得超生的。
中共當時加入聯合國不久,把美國的毛派反帝年輕學者請來參訪,是個重要的統戰任務。在反越戰氛圍中高舉「反帝反殖」大旗的年輕毛派眼裡,中國能夠在國際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陣營對抗之外,走出一條另類革命道路,是令人欽佩的。他們對於當時的文革語言倍感親切,認為廣大的群眾已擁有必要的知識,需要的只是自求解放,打倒壓得人喘不過氣的官僚主義。中國人民不需要專業精英來治國(知識越多越反動)。所以在中國大陸,知青下鄉,教授專家下放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在他們看來,是順理成章的。
這批毛派的「關切學者」,在毛澤東駕崩,民怨排山倒海地在中國大陸湧現後,很快就陷入了窘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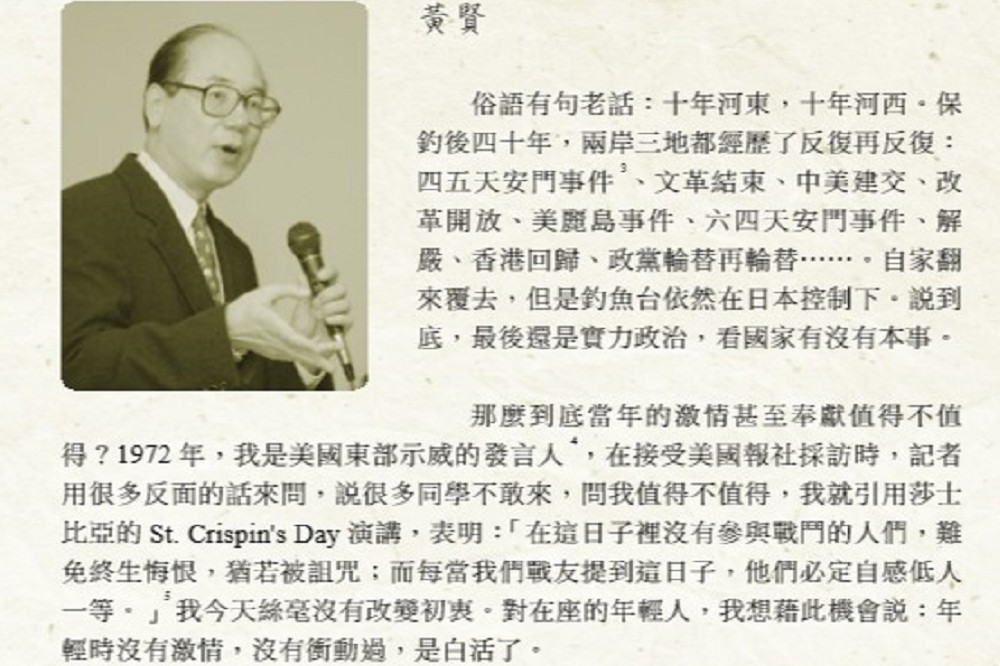
無獨有偶,在這批美國的「關切學者」造訪中國之前,在美國參加保釣運動的台灣學生領袖也經由中共駐加拿大使館的安排,受邀前往北京參加國慶觀禮。第一批學生5人,1971年9月下旬經羅湖入境大陸,被稱為保釣零團。他們抱著朝聖的心情被官方安排去參觀大慶大寨等革命聖地。
在保釣零團之後,1972年有保釣一團,來自香港在美國哈佛大學就讀的保釣學生領袖黃賢,就是保釣一團的成員。
黃賢雖然也有民族主義熱情,但他卻是理性務實的,不是那種懷抱朝聖的心情去吃政治拜拜的人物。因他的香港身份,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喬冠華在北京宴會上拉他坐在旁邊,討論台灣香港問題,他直言無諱地斗膽表達與中共官方不同的看法。黃賢強調,統一或回歸,應是攻心服眾,不是攻城掠地。人民是主體,不是被動的受體。他的觀點當時立即惹來中共中央調查部(外稱「西苑中直機關」)高層的反對。但他依然堅持觀點,談話幾乎不歡而散。事後他頗爲感慨地指出,共產黨立國於「鬥爭哲學」,常態是左傾、排外,沒事炮製各色內、外敵人,免不了還會反覆。黃賢認爲,不論什麽政策,最後都須接受現實的考驗。政策能否得人心,措施能否到位,操作的官員能否勝任,都是不能不思考的問題。在他看來,中共高層容易被所謂「外國勢力」、「國家安全」煽動綁架;容易相信投其所好但查無實據的分析。稍許不慎,日後就必定要付出代價。
香港在九七回歸後的一連串演變,無疑可作為黃賢當年的觀察的注腳。香港回歸後,爲什麽會落到今日這步田地?昔日的國際金融中心如今在外人眼中淪為一個遺址、廢墟。這難道不是其來有自的嗎?
黃賢在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後,回香港加入一家著名的律師事務所Baker & McKenzie。但他報效國家的愛國心,驅使他甘願放棄香港安逸優渥的生活,到北京大學去從事法律教學。教學期間,上海一位老先生汪道涵建議他去幫一位「年輕人」江澤民做事。這是他涉足中國大陸的實際政治的開始,也是他日後遭受橫逆,落得在秦城監獄坐牢的一段荒謬經歷的由來。
中國第一家中外工業合資企業是江澤民和黃賢一起審查的。江性格十分愛現,有時候在開會會時忍不住要賣弄幾句英文,黃賢忍不住要在台下輕踢他幾腳,提醒他收口。黃賢參與的工作是經貿部門的改造。他受邀當顧問,離開了Baker & McKenzie,投入大陸的政治漩渦中。
要將經貿大衙門內許多疊床架屋的部門裁併精簡,增加運作效率,難免會觸動中共官僚體制中最難纏的山頭主義。被裁併的部門首長心懷怨恨,就要尋思報復。黃賢這個年輕的外來者,既參加了會議,又閲讀了相關工作文件(「國務院二號文件」以及江澤民主持的聽證會資料),就成爲他的「罪狀」。
對意圖挾怨報復的人來説,他正是可以輕易下手的對象。這就是他從協助整改的客卿變成竊取國家機密的外來間諜的緣由。他被定了罪,1982年進了秦城監獄,即使江澤民想救他也要大費周章。部門山頭之間明爭暗鬥不説,即使能夠設法一一擺平,也還得要被囚者寫認罪書,因爲黨和國家是不可能犯錯的。偏偏黃賢又是個固執的實心漢,始終堅持自己清白無辜,拒絕認罪。就這樣在秦城監獄裏蹲了一段相當長的時日,一直到八九六四後江澤民掌大權,爲他平反出獄爲止。
黃賢返港後,除了從事法律事務外,他還是一個政論家。在香港政爭事件發生時,他提筆為文,站在香港基本法的立場,解析傳統普通法的法理原則,為香港的泛民主派辯護。
2021年,老友李怡爲完成回憶錄自港來臺,也告訴我一些關於黃賢的近況。他在香港的生活似乎悠閑安逸,很值得慶幸。他的經歷,不免也令我想起小説家白樺所描述的那種對祖國的「苦戀」。你愛那個國家,但那個國家愛你嗎?
黃賢和我那從未謀面的短命岳父一樣,都是香港拔萃書院的畢業生。
※作者為前香港《九十年代》專欄作家,著有《最後一個租界:香港變局紀事》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趙麗穎與《玫瑰的故事》林更新爆熱戀 她帶兒子看煙火他「這穿搭」現身放閃
- 趙麗穎與《玫瑰的故事》林更新被抓包穿情侶裝 兩人隔空示愛3證據曝光全網沸騰
- 張若昀《慶餘年》第二季流量奪冠成劇王 他開2千萬跑車因「這舉動」形象全毀
- 【有片】中華隊球員「無敵星星」吊飾哪裡買?博客來明日早上再次開放預購
- 《長相思》檀健次開唱勁歌熱舞嗨翻 卻被抓包在台上做「這件事」超噁心掀罵聲
- 《永夜星河》虞書欣新劇停拍3天劇組全換人 官方海報獨厚她卻沒男主角內幕曝光
- 譚松韻《蜀錦人家》與鄭業成吻戲被刪光掀眾怒 2敗筆熱度慘輸孟子義新劇《九重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