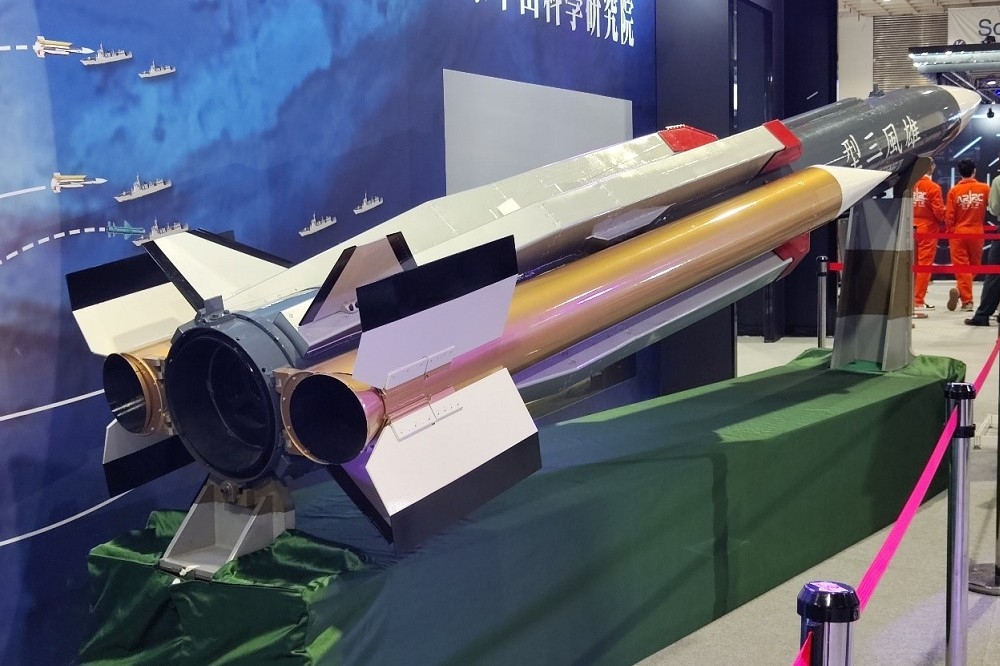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慶餘年》李沁新劇虐戀《蓮花樓》曾舜晞預告曝光 她5字暗示兩人天人永隔全網揪心 2024-04-29 11:00
- 最新消息 狂灌不停!全台水庫1天進帳1425萬噸 德基水庫水量衝破6成 2024-04-29 10:35
- 最新消息 基泰大直「偷工減料」又偽造鄰損認定 工地負責人、主任、建築師等5人遭起訴 2024-04-29 10:33
- 最新消息 《淚之女王》大結局24.9%收視超越《愛的迫降》 金秀賢、金智媛無憂宮前深吻觀眾喊不夠看 2024-04-29 09:33
- 最新消息 高雄漢來海港巨蛋店食安疑慮增至50人 「風險用餐時間」再擴大 2024-04-29 09:27
- 最新消息 星巴克限時兩天買一送一!51勞動節加碼第二杯半價優惠 2024-04-29 09:00
- 最新消息 【有片】日本眾議院補選立憲民主黨3席全贏 鐵票區失利岸田內閣蒙陰影 2024-04-29 08:59
- 最新消息 直播/傅崐萁率16藍委訪中 8:50記者會說明成果 2024-04-29 08:50
- 最新消息 歡慶五週年!《五等分的新娘》特報公開,新作動畫「新婚旅行篇」製作確定 2024-04-29 08:30
- 最新消息 【有片】美中部惡劣天候影響4700萬人 龍捲風襲奧克拉荷馬州釀4死 2024-04-29 08:24
輔大心理系性侵案所突顯出的,不只是一般性侵被害人欠缺可信度的處境,還有性侵害的受害者政治。於是,這個案件所出現的戰爭,還包括性權派(sex-positivists)將受害者論述視為性壓抑的產物,主張絕對自由的情慾解放、強調個人主體培力、反對國家保護的意識型態戰爭。(攝影:陳品佑)
許多犯罪是有加害人也有被害人的犯罪。生命、健康、財產與自由被奪走的被害人,在述說受害的苦痛時,她/他們的經驗與感受一般被認為是真實的存在,很少有人用「踩在一個受害者的位置上」這樣的說法來指責犯罪被害人,反對她/他們說出「一個受害者的版本」。人們一般也認為,犯罪乃是加害人對被害人造成傷害,必須為此負責。
性侵害犯罪卻常是有人認為被害,卻無人承認加害的情況,因為受害者通常欠缺可信度。性侵害的事實經常籠罩於「雙方各執一詞」、「其實是你情我願」、「事後反悔」的迷霧中,成為受害者與加害人的「可信度戰爭」(誰的說法比較可信?)、「觀點戰爭」(她說到他家喝酒聊天不等於答應上床,他認為答應到自家喝酒聊天就是答應要上床),甚至被指控為虛構誣陷的鬧劇或陰謀。
輔大性侵案被害人受害的真實性被否認的遭遇絕非例外個案,但這個案件所突顯出的,不只是一般性侵被害人欠缺可信度的處境,還有性侵害的受害者政治:性是否應該是愉悅,而非是危險?主張遭受性侵害,是否就等於「性壓抑」、情慾不解放?自認為受害者,是否就否認了自己的主體能動性?尋求體制的介入追究責任,是否就等於要求國家父權的保護?於是,在這個案件所出現的戰爭,不只是性侵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可信度和觀點之爭,還包括性權派(sex-positivists)將受害者論述視為性壓抑的產物,主張絕對自由的情慾解放、強調個人主體培力、反對國家保護的意識型態戰爭。
就是在這樣的受害者政治脈絡下,輔大性侵案的被害人經歷了種種令人瞠目結舌、匪夷所思的對待,讓她必須為自己被指控的「加害行為」公開道歉,做出「加害者」的自白,以鞏固特定性權論述的正確性。另一方面,公眾的撻伐則被性權派當作性少數遭受保守派打壓的證據,主張特定性權論述、反對被害者論述的教師,卻爭奪被害者的位置,提出被害者敘事,自認為遭受保守民粹的政治迫害。
「性權派」與「婦權派」錯誤對立
性侵害的受害者政治,不是今天才出現。「性權派」與「婦權派」錯誤對立,就是臺灣性政治的最初產物之一。為了凸顯情慾解放的進步性並賦予性解放特定的定義,性權派將「反對性壓迫」當成「主張性壓抑」,為與之立場不同的女性主義運動者安上了「婦權派」的名號,聲稱她們反「性」、主張性壓抑、提倡良家婦女觀、要求國家父權保護,無視於這些女性主義運動者對良家婦女觀的批判、對性自主權的支持、以及對改變國家父權的努力。
然而,性解放的實踐,不應建立在平等的條件之上嗎?反對性侵害,為何就是反對「性」?要求以平等條件為基礎的性自由,為何變成主張性壓抑?主張改變國家法律以實踐平等與自由,為何被一概等同於壯大國家打壓個人自由?
我們可以從「受害者女性主義」(victim feminism,簡稱VF)和「反-受害者女性主義」(anti-“victim feminism”,簡稱AVF)的錯誤對立來認識這樣的性政治。AVF創造出VF的說法,宣稱這種女性主義將女人視為本質上的受害者,聲稱其在理論上與實踐上教導女人被動不反抗,性是危險而不可能是愉悅,無助的女人需要國家來保護。對於主張並推動以國家和法律來改變性別不平等的女性主義,AVF甚至為之貼上「治理女性主義」(governance feminism,簡稱GF)的標籤,批評其已取得莫大的國家權力、並聯合國家來壓迫個人自主。
AVF認為VF與GF是錯的,女人已經不再是被壓迫的群體,而是具有充分自主性的、能夠自由選擇與行動的個人,所謂受害其實是自己不懂得反抗、或者是太保守想不開的結果,訴諸國家更是強化國家父權的控制。在AVF來看,應該把「受害者論述」擺一邊,實踐解放的「抗爭主體」才是王道。於是,受害者成為欠缺主體性的代名詞,主張受害性等於沒有主體能動性;是行動主體就不應該採用受害者論述,也不應該讓國家取得干預私人情慾空間的機會。
輔大性侵案的荒唐發展暴露AVF問題所在
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輔大性侵案的被害人會被指責「踩在一個被害者的位置上」、會不被允許敘說「一個被害者的版本」,性平與司法機制會被視為無用甚至有害的管道。然而,也正是輔大性侵案的荒唐發展,鮮明地暴露了AVF的問題所在:強調主體性卻變成譴責被害人(blaming the victim),追求抵抗與培力(empowerment)卻以否定壓迫存在為前提,追求自治卻與強調個人責任與市場功能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不謀而合。
然而,強調培力不需要否定壓迫,說出被害的故事並要求正義是主體能動性的展現;被害人不應該被怪罪譴責,彷彿受害是她自找的或虛構的想像,想開了就沒事;著重私人解決而反對國家介入,不僅容易淪為既有壓迫結構的幫兇,甚至可能製造新的壓迫(工作小組與百人的「溝通」馬拉松大會即為其例)。我們可以檢討司法與性平機制運作的缺失、法律規範的問題,但比起開地圖砲(網路上針對某個群體進行大規模言語攻擊的行為)反國家,追求制度保障的改善更能改變在既有權力關係中弱勢者受壓迫的處境。
AVF不僅建立了被害性與主體性的錯誤對立、虛構了假敵人VF和GF,更因為漠視權力與現實,而讓自己成為壓迫的一部份。如果正視權力,就會看到在各種關係中的權力位置不對等;如果面對現實,就會發現性的現實不是只有自主的實踐,還有壓迫的存在。強調個人的意志、選擇與行動,固然有助於提升個人自主性,但因為重視個人主體性而輕忽結構上的權力不對等、頌揚解放而否認壓迫現實的結果,卻正否定了被害者的主體性,她說出的傷害不被承認為傷害,她的傷害沒有加害者(如果有,那正是她自己)。
這讓我們回到性侵害是「有受害者而無加害者」的犯罪這個問題。女性主義法學者Catharine A. MacKinnon曾以「女人被強暴了,但卻不是強暴犯做的」(A woman is raped but not by a rapist)來說明性侵害法造成「有受害者而無加害者」的狀態。這不是指確實有犯罪、卻抓不到罪犯的情況。她的意思是:當女人主張自己被強暴的時候,強暴她的人說這不是強暴,而眾人與法律也傾向於採用他的觀點說這不是強暴。臺灣的性侵害法對於強暴的定義從「不能抗拒」到「違反意願」的轉變,是從加害者觀點轉為受害者觀點來定義強暴的結果。
這個轉變並不理想,因為「違反意願」定義為「積極的拒絕」,因此無法有效地改變女人被「推定同意」(沒說不,應該就是要)、被課以「盡力表達拒絕的義務」的狀態。在很多時候,性侵害仍是有受害者而無加害者的犯罪,而為了改變這樣的狀態,臺灣在近年來開始出現採行「積極同意」(affirmative consent)模式的倡議。雖然「積極同意」模式並非性侵害法改革的唯一途徑,將焦點集中在意願也有一些風險,但此模式值得我們仔細思考。
「別當這樣的男人」vs「別當這樣的女孩」
國際上採用「積極同意」模式的著例是加拿大,其於1992年修改刑法性侵害的定義,將同意定義為當事人的自願同意(voluntary agreement),不能由其他人代為表達、也不能是利用權勢地位的結果,而且在同意開始性行為之後,還是可以在過程中拒絕繼續進行。加拿大法院也以數個指標性判決認定:沈默不是同意,預先同意也不算數,同意必須是意識清醒的人在性過程的每個階段中所為的積極同意。
這種強調在具體脈絡條件中認定意願的立法模式在近年來的臺灣與美國都獲得一些支持,但也都遭遇了反對。有些「積極同意」模式的反對者,斥之為壓抑情慾的保守立法,認為這是在壓抑性的自由實踐、鼓吹女人不用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可以隨意反悔。這類反對者不僅虛構出「積極同意要求進行性行為得先簽同意書」的荒謬指控,更自認男人已成為性侵害法的階下囚。
加拿大的女性主義運動發起一系列反性侵害宣傳「別當這樣的男人」(Don’t be that guy),用以提倡尊重女性的性自主權,例如倡導「送酒醉的女人回家,不表示可以對她為所欲為」。為了反制這種性自主權的倡議,主張女人是男人性物的男權運動者仿照製作了一系列「別當這樣的女孩」(Don’t be that girl)海報,主張女人應該為自己的性行為決定負責,不能拿酒醉或反悔當藉口。這兩張海報,不正說明了對輔大性侵案的兩種不同觀點嗎?這不也正顯示了,性權派與男權運動令人難以分辨之處?


性侵害的受害者政治,在輔大性侵害中發揮到極致,也因此得到社會前所未有的注意。然而,極端的矚目個案所激起的集體憤慨,是否能轉化為對性侵害的重新認識、對權力與壓迫現實的根本反省、對性侵害法的基進改革?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於公眾討論的方向以及行動的選擇,是否能夠正視性侵害的現實與權力配置,拋棄受害者與主體性的虛假對立,避免與男權運動和新自由主義的同床共枕,並且在此前提之上,追求性侵害法的根本革新,讓平等成為性自由的條件,而非為了某些人的性自由、犧牲其他人的性平等與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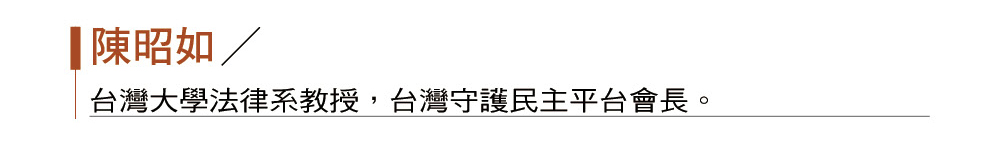
【上報徵稿】
上報歡迎各界投書,來稿請寄至editor@upmedia.mg,並請附上真實姓名、聯絡方式與職業身份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