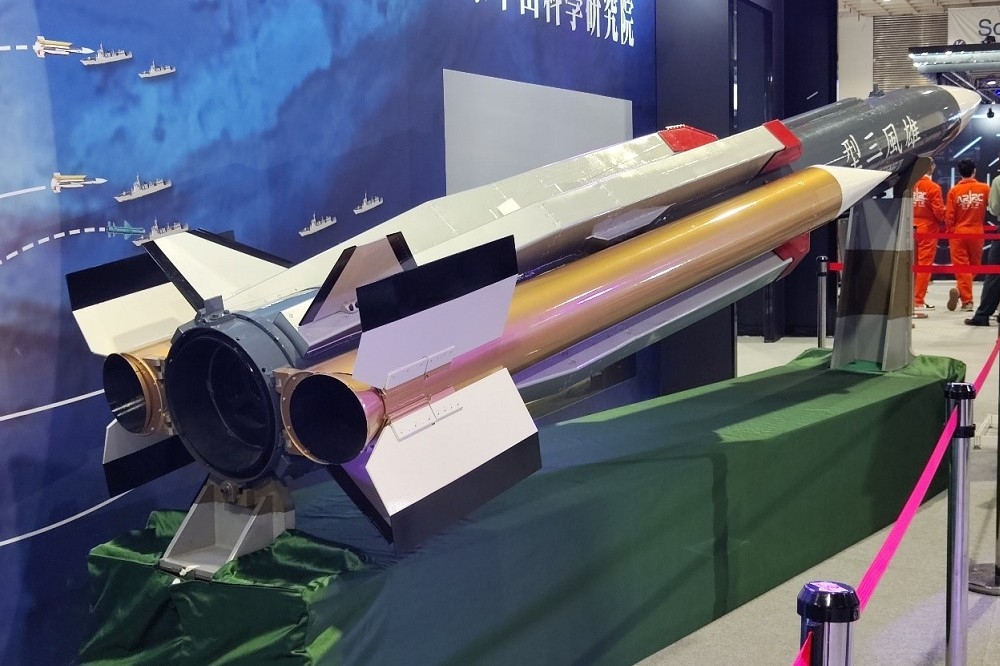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好痛! 讓我們在《不夠善良的我們》裡找餘味 2024-04-28 23:20
- 最新消息 馬陸大軍遷徒大地震前兆? 雪霸休閒農場曝光原因 2024-04-28 21:56
- 最新消息 花蓮慈濟醫師賞鯨離奇失蹤 東澳外海尋獲遺體死因曝光 2024-04-28 21:35
- 最新消息 《絕地求生》經典 Erangel 地圖即將重返絕地戰場, 回歸最初的感動,回家吃雞囉! 2024-04-28 19:29
- 最新消息 統測英語考題涉抄外國網站「一字未改」 測驗中心:疑義提交討論 2024-04-28 19:00
- 最新消息 美海軍近岸作戰艦「坎培拉號」搭載最新反水雷模組 盼汰換老舊掃雷艦 2024-04-28 18:50
- 最新消息 提升M1A2T戰車夜戰效能 陸軍規劃夜視系統擴及駕駛員 2024-04-28 18:45
- 最新消息 【一周天氣預報】又有鋒面來襲!明高溫上看36度 周三起迎大雨 2024-04-28 18:45
- 最新消息 高雄漢來自助餐增至46人餐後腹瀉 疑生熟食混用停業清消 2024-04-28 18:41
- 最新消息 中國恢復福建居民赴馬祖旅遊 陸委會:不符合對等開放 2024-04-28 18:33

今天全中國約有兩億左右的佛教與道教徒。就連處處受到中共掣肘的基督教,據估計都多達將近六千萬信徒,在1949年之後以每年7%的速度增加。(北京分鐘寺/圖片取自百度百科)
倪金城領著我沿著一條小街,拐進一條連汽車都開不進來的狹窄胡同裡。他推開我們右手邊的第二扇門,三條小狗衝過來,邊搖尾巴邊對著我們吠叫。他從第一個房間門口走過,他的妻子和另外三個女人正圍著一張暗色紫檀木牌桌上打麻將。她們抬頭看向我們這邊,出聲打招呼,端上茶和葵瓜子,我連忙揮手表示感謝。倪金城輕手輕腳地打開了一扇玻璃門,我們就進到後面那個房間,他的父親坐在房裡一張沉重的木質雕刻座椅上等候我們——這張座椅正是這位北京宗教界大老的寶座。
倪老剃了個光頭,臉上一道濃黑的八字眉,看上去永遠是謙遜的模樣。他愛和人講捉蟋蟀、蒐集葫蘆和養狗經。幾個月前我來拜訪他的時候,我們從書法開始談,一直到他年輕時候就投身的工程建設事業,一連聊了好幾個小時。上回倪老告訴我,他得了癌症,不過他堅信自己一定會康復。不過,這一次,我可以看出病痛正在壓垮他的身體。他的雙手緊緊攥住座椅的扶手,彷彿掙扎著要挺直身體。他的頭靜靜的垂著,我走到他跟前,他卻一動也不動。他費了好一番工夫,才睜開眼睛,比了一個手勢,要我在他旁邊坐下。然後,他鼓足全身的力氣,開始發號施令,對我說道:
「你想寫書,首先得把事實搞清楚。要不你寫出東西來,別像北京電視台,胡說。別誤人子弟,知道嗎?」
我回想過去自己幾次到妙峰山,電視台通常拍攝的是有趣的喜慶活動,報導的是傳統中國文化裡的每件事物是如何的美好。電視台很少呈現人們敬拜神明的畫面,而且避免提及這是一場大型的宗教廟會活動,看起來就像是在報導一座主題公園的全新開幕。於是我點了點頭。
「我身子骨不行了,也不知道能不能什麼都給你講清楚。我跟你講,把你引導錯了,你要再寫出東西來,不更把別人也帶錯了嗎?然後離真相越來越遠。」
「廟會的東西,你要記住了,本身的性質和別的不一樣。你寫書的時候,得分是什麼樣的廟會。想要去廟會看看民間花會,得知道都有什麼會。妙峰山的廟允許你走花會,有的廟就不允許你走花會。所以我們的就去那。」
倪金城彎下身子,在我耳邊輕聲提醒道,他家辦的茶會是怎麼創立的。那是在一九九三年,當時倪老病了,被診斷罹患腎癌,必須立刻動手術。他立下誓願,如果他能度過這一關,就要去妙峰山答謝碧霞元君。祂在老家時就已經庇護過倪家,倪老相信這次神明也會幫助他。回到家裡,倪金城便焚香祝禱。
手術相當成功,倪老順利恢復健康。隔年春天,他便上妙峰山去還願。雖然倪家從前就住在碧霞元君的道觀附近,卻從來沒有上妙峰山的廟會進香過。日本人侵華的時候,倪老才八歲;共產黨得天下時,他也只有二十歲。在這些動盪不安的年代裡,前來進香朝聖的人潮萎縮到只剩下涓滴細流,因為人們不但有安全方面的顧慮,而且通常還因為太過貧困,以至於無法負擔一路到妙峰山上朝拜的費用。毛澤東掌權之後,他的狂熱追隨者將妙峰山的主廟摧毀。不過到了一九九○年代中期,主廟已經重建,廟會進香活動也恢復舉行。
在還願下山的途中,倪老告訴大兒子金城,自己有個想法。他想要辦一個茶會,向上山進香的信徒奉茶。從字面意思來看,這類茶會是多餘之舉;時至今日,上山進香朝拜通常只需一天時間,沒有人需要免費的茶水或食物。但是茶會仍然存在,因為興辦茶會背後的想法,遠比它實際的功能來得重要。茶會象徵信仰的虔誠——一群有真摯信仰的人聚集起來,奉獻上萬塊錢和好幾個星期的時間,就為了辦好一個奉茶水的茶會。
倪金城聽了,停下腳步一會兒來思考。辦這樣一件事可能會花去大筆的金錢。他們需要一座小廟壇,裡面供奉精美的神像和一座祭壇。在小廟的前面,還需要擺放一套昂貴的陶瓷茶壺與茶杯,表示這裡提供茶水。當然,他們還需要大量的茶,而且不能是廉價茶,要能夠展現對碧霞元君的虔敬才行。然後,他們還需要照顧攤位的志工幹部,好讓進香的信徒隨時都能取用茶水。這些準備可得要花上幾萬元人民幣,特別是對那個時候的勞動階級人民來說,那可是一大筆錢。不過倪金城當時已經在私營企業工作,而且開始在建設業界獲利。他還知道,自己可以仰仗家人和朋友的協助。於是他看著父親,點頭表示同意。在一九九五年那次的廟會上,他們以自己原來的積蓄,加上朋友、同事的捐獻,開始在妙峰山上為信徒提供茶水和包子。
現在我望向倪老,並且點了點頭:我知道這段故事,而且我還知道,正因為是妙峰山,他才辦了這個奉茶的茶會。
「您二十年前就好了,這次奇蹟也許可以再來一次?」我大膽的探問道。
他搖了搖頭:現在不是說空話的時候。他自知來日無多,而他想要將自己覺得重要的事物流傳下來,讓後人明白。他的聲音直到去年夏天時都還強健清朗,可是現在卻沙啞得很。他費力的憋足張嘴說話的力氣。
「你得看你要寫民俗去拿錢、掙錢,還是寫民間的信仰。」他盯著地板說道。然後,他做了一次深呼吸,開始提起沒人敢說的事情:文化大革命,那對宗教帶來混亂和破壞的十年。像妙峰山這樣的廟宇,都被夷為平地,道士、比丘和比丘尼遭到羞辱、驅離。而當動亂隨著毛澤東於一九七六年死亡而結束時,人們的宗教生活緩緩地開始復甦。
「十年浩劫過來,國家也不支持恢復,也沒反對,基本是默認。也沒有哪個文件說不可以,也沒有支持,就是默認。懂嗎?就是民間自發恢復的。」
「『民間』倆字兒,」他說道,停頓下來,讓這兩個字在空中多停留幾秒鐘:「代表不管你是誰,不管你是農民還是什麼,都行。」
「但是現在,」我說:「你們恢復這些傳統的第一代已經老了。你的孩子會不會繼續?」
「人哪……,」他思索著,聲音漸漸變小,試著想從腦海裡找出一個準確的表達方式。「做善事是沒有頭兒的,沒有終點的。你看你是西方人吧?不管你是天主教還是新教,沒有說信三十年,老了就吹了,不可能。記住這個,凡是信仰什麼,沒有半途就到終點的,一直送你到終,這才到終點。下一步呢,你的子女再接你留下的東西。基督教也是一樣。」
「任何信仰都是這樣。」倪金城在一旁補充道。
「你明白這個道理嗎?性質是一樣的。一說明白,這裡面沒有什麼奧妙。當然,中國的文學和中國的各方面文化,那真是博大。吃文化、喝文化、住文化都不一樣。哪方面能把它看透,那可不簡單。」
「信仰就不一樣了。本質是很簡單的,只是具體細節不同而已。」老人突然氣喘吁吁,雙手使勁撐著,想讓自己坐直。倪金城的妻子陳金尚走過來,用手扶住公公的肩頭,幫他坐穩。
「來,您歇會兒的,」倪金城輕聲細語地對父親說道。老人搖了搖頭。
「跟我聊那些文化,純粹是瞎耽誤功夫。」他笑著振作起身子。「我這人還不愛瞎說八道,知之為知之,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要問什麼就問吧。」
「我想知道您為什麼還在組織這個茶會。」我說道:「您想要答謝碧霞元君,因為她救了您的命。」見他點了點頭,於是我繼續說下去:「但是您為什麼年復一年地去?難道是還沒有答謝夠嗎?」
「需求是有的。有些人啊,有點心神不寧的。他們來到山上,我們就得恭候。我們要把這個傳統傳給下一代。我覺得這是我的一個責任。」
他暫停下來,思索著怎麼措辭。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廟的歷史也算是有故事吧,因為總有名人去給這個廟進香。你知道程硯秋嗎?京劇的四大名旦之一,很了不起。他給捐獻過一個香爐,很有名,這已經是歷史的一部分了。」
「那些都是名人,但是你留下的管多大用啊?」他問自己:「誰認得你啊?你留什麼不也就那麼回事嗎?」
然後他回答自己提出來的問題。
「除非我留下這個茶會。咱們這個『全心向善結緣茶會』跟所有茶會的名字都不一樣,我們是以善為本。」
「你到底會留下點什麼?」他又自問了一次,然後以一種不同以往的深沉聲音回答。
「你有你的茶會。」
「哎,對了!北京市豐台區分鐘寺這邊有一個『全心向善結緣茶會』。沒錯,你可以把這個留下。」
「我,倪振山,可以把這個留下。否則誰認得你啊?」
倪金城的眼睛盯著地上看。他的父親已經在談自己的身後事了。這讓他很擔心;要是他父親過世了,誰還要把這個茶會辦下去啊?
「爸,您這話怎麼說呢?瞎說八道!」倪金城的妻子突然開口了。陳金尚今年五十六歲,是位個性活潑的婦女,留著一頭燙捲的短髮,還有著開朗宏亮的笑聲。但是,她的公公現在這麼說,讓她擔心煩惱。
老人顯得很有耐心;眼前這人是他的兒媳婦,成為倪家人也已經有三十年了,金尚是個忠誠孝敬的好女人,過去幾個月來不分日夜的照料著他。該怎麼解釋,好讓她明白呢?於是,他想到家族的功德碑——這是一塊一公尺多高的石碑,豎立在妙峰山主廟外面,表彰倪家興辦茶會,為上山進香的信眾提供茶水。石碑的前頭鑿刻茶會的名稱。後頭則刻有創辦時的家族成員姓名,也包括她。倪老慈愛的看著她。
「這東西,將來哪怕廟主換了,咱這個『功德碑』也不會給扔了。將來誰要一提呢?陳金尚,知道啊,她就是那個『全心向善結緣茶會』的兒媳婦啊。要是沒有那個東西,你在歷史上就留不下名。」
「爸,再過多少年,這碑也經不住風雨,要折要倒的啊。」陳金尚說道。
「是這樣呀,但是得讓老天知道你的功德啊。將來你的孫子還繼續在妙峰山擺茶會,他一看這碑不成了,就會重整,立一個新的,並且還得把名字刻下來。你們家的重孫子到時候就知道他祖奶奶叫陳金尚,走過妙峰山,在這兒立過一個碑。他們那輩重新再立碑,再重整,這就是『一傳萬年』、『萬古千秋』!」
「本來啊,我爸還想出本關於這個的書呢。」陳金尚對我說道。
「恐怕你想得到的東西,我知道也不是特別多。」倪老說道:「我本身沒那麼高文化,胡說八道,你再寫出去就是誤人了。」
「你寫的這本書,」他的兒子很睿智地點頭說道:「如茫茫大海一般。」
「你要了解茶會的哪個方面?」老人向我問道。
「你需要人點撥點撥,」他的兒子補充道。
「你到底在寫什麼啊?」老人的兒媳婦大笑著問,然後我們所有人也跟著大笑了起來。
「我想寫人們信仰的重生,」我告訴他們,「信仰在文革後恢復了不少,近些年來發展得很快。」
「這就像我啊。」倪老表示:「遇到挫折,有了病,我就有了這個信仰。這一輩子第一次不缺錢了,所以我就去帶點茶。那時候也是『各懷心頭事,計在不言中』。你今天讓我上山,看看今年茶會怎麼樣,缺什麼,明年再補什麼。我就是看看能幫上什麼忙。今年我們帶的綠茶。」
「我爸爸那個時候,這個綠茶特貴,所以我們茶會就傳下來了。」倪金城說:「這就是為什麼有綠茶。但是茶會和茶會的規矩還不一樣,我們這也是在遵循佛教的布施。」
「好多這種新玩意兒都是為了掙錢的。」倪金城又加上一句,「根本不是那麼回事。」
接著,出乎我意料的,倪金城的老父不認同這個看法。
「可別這麼說,」他表示,堅定地搖著頭,他的濃眉皺在一起,彷彿是對這個看法進行過一番深思,然後決定不予認可。「並不是所有新的東西都不行。有的新的形式發展起來,過了一代後也是老的了,最後能變成傳統。」
 ※本文摘自《中國的靈魂 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北京:分鐘寺/八旗文化出版/作者是2001年美國普立茲獎得主,善於社會、政治、宗教議題的報導。常駐於北京,並於當地大學授課。出生於加拿大蒙特婁,在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取得新聞學和亞洲研究學位。他在1984年至1985年期間以學生身分在北京生活了一年,這是他第一次到中國。1986年至1988年期間曾造訪台北。1994至1996年期間,他被巴爾的摩《太陽報》派駐於北京,擔任通信員。1997至2001年期間他服務於《華爾街日報》,負責中國經濟改革、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及各種社會議題。2009年張彥為《紐約時報》服務時再度回到中國,並在「北京中國研究中心」(The Beijing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等機構教書,同時擔任諸如《亞洲研究月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等學術期刊與智庫的顧問。
※本文摘自《中國的靈魂 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北京:分鐘寺/八旗文化出版/作者是2001年美國普立茲獎得主,善於社會、政治、宗教議題的報導。常駐於北京,並於當地大學授課。出生於加拿大蒙特婁,在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取得新聞學和亞洲研究學位。他在1984年至1985年期間以學生身分在北京生活了一年,這是他第一次到中國。1986年至1988年期間曾造訪台北。1994至1996年期間,他被巴爾的摩《太陽報》派駐於北京,擔任通信員。1997至2001年期間他服務於《華爾街日報》,負責中國經濟改革、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及各種社會議題。2009年張彥為《紐約時報》服務時再度回到中國,並在「北京中國研究中心」(The Beijing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等機構教書,同時擔任諸如《亞洲研究月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等學術期刊與智庫的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