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中國通過新關稅法反擊貿易制裁 專家:效果如同核彈 2024-04-26 17:40
- 最新消息 今率16位藍委訪中 國民黨團總召傅崐萁:我們會勇往直前 2024-04-26 17:34
- 最新消息 前女友找不到NBA「公牛隊紀念外套」 離譜男竟威脅要外流性愛影片 2024-04-26 17:22
- 最新消息 美國會議員挺黎智英 提案將駐華府香港經貿辦地址改為「黎智英路1號」 2024-04-26 17:15
- 最新消息 黃國昌立院內爆衝突 狂怒對范雲咆哮:我有欠你喔? 2024-04-26 17:08
- 最新消息 逮到人!領藥單印「媽媽是婊子」人妻傻眼 基隆醫院藥劑師犯案請辭 2024-04-26 16:45
- 最新消息 楊冪《哈爾濱一九四四》帶表演老師貼身指導演技仍爛爆 為戲真甩對手3巴掌急道歉 2024-04-26 16:36
- 最新消息 亞洲U20田徑賽傳佳績 標槍女將朱品薰、戴佑芩斬獲「金包銀」 2024-04-26 16:27
- 最新消息 【獨家】傅崐萁率藍委團「進京」 明午人民大會堂會見王滬寧、宋濤 2024-04-26 16:25
- 最新消息 黃世杰立委連任失利轉入閣 傳將接法務部政務次長 2024-04-26 16:23

歷代德國人所說的征服自然,換一個軍事隱喻也能貼切表達,也就是一連串的水的戰爭。(德國巴伐利亞州的米斯巴/美聯社)
德國士兵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出征時,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誓言他們將在秋葉落下前凱旋返鄉。時至一九一五年,士兵與平民都不得不認清,德國將無法如此輕易地讓敵人臣服於其意志下。
那一年,作家威廉.布榭(Wilhelm Bölsche)出版了《德國地貌昔與今》(The German Landscape Past and Present)一書。布榭是二十世紀早期德國著名的社會改革者,他推廣達爾文的理論,也是田園城市(Garden City)運動的創始成員之一。
該運動提倡的是:德國日益擴張的城市中,應有更多綠色空間。這本書是布榭對戰爭大業的貢獻,也是要動員自然為國家目標服務的眾多嘗試之一,書前的序言把這個訊息傳達得清楚明白。序言作者是同為社會改革者的法蘭茲.高爾基(Franz Goerke),他關心科學普及教育,也對自然保育這類「綠色」使命懷抱熱情。「在這個奮鬥與作戰的時代,」高爾基寫道,德國的地貌「是我們必須捍衛的最偉大的事物。」
對數百萬曾參與二十世紀戰爭的德國人而言,這樣召喚他們犧牲的話語並不陌生。需要他們捍衛的地貌是「德國偉大的綠色田園」,是他們的原鄉(Heimat),其草原、樹林與蜿蜒溪流是德國民族性與精神的搖籃。不論戰爭可能帶來什麼巨變,自然地貌──正如其所滋養的人們一樣──總是會在那裡,讓人安心,永恆不變。
只是,它當然並非永恆不變。一九一五或一九四○年的德國人如果回到一七五○年,一定會為「自然」地貌在當時有多麼不同而震驚──耕地很少,由沙、灌叢,特別是水所占據的土地則多得多。來自二十世紀的訪客無須走太遠,就會碰上早已被排乾和遺忘的水潭、池塘與湖泊。
回到了一個失落的世界
來到在十八世紀仍廣泛分布於北德平原的低地草澤和沼澤地,現代的旅人可能會完全迷失方向。受過教育的當代人將這些地方比為新世界的溼地、甚至是亞馬遜盆地,不是沒有原因。這是片陰暗的水鄉澤國,充滿被懸垂的藤蔓掩蔽、只能乘平底船通過的曲折水道,這裡是蚊子、青蛙、魚、野豬與狼居住的地方。
與二十世紀德國人所熟悉、有著風車與整齊原野的開放地貌相較,這裡不僅看起來很不一樣,連聞起來、聽起來也很不同。任何一座德國河谷內的現代旅人一定都會覺得,自己回到了一個失落的世界。在一七五○年,河流本身看起來很不一樣,連流經之處都和現代不同。現代由工程改造的單一水道,在兩側堤岸間快速流動,形成交通動脈,大大不同於十八世紀的河流,其時河流蜿蜒漫流於氾濫平原,或者在數百個由沙洲、礫石岸與島嶼分隔的水道中前進。
它流動得迅速或緩慢依季節而定,而非依照全年通航所需要的節奏而定。沿著河流兩岸綿延數公里的是尚未被耕地與工業設施取代的溼地森林。這是萊茵河在十八世紀的樣貌。歌德在那條河中釣鮭魚,數百人在那裡的礫石中淘洗黃金。萊茵河在其後的一百五十年成為德國身分認同的最高象徵,但那已是一條新的、不同的河流了,沒有鮭魚和萊茵黃金容身之處。
上面描述的是一七五○年左右的低地德國,多數景物在二十世紀的觀者眼中幾乎難以辨認。高地德國改變得比較少,但還是足以讓我們這位假想的旅人目瞪口呆。比如,想像這位旅人是一個在二十世紀的東夫里士蘭半島(East Friesland peninsula)、或是在曾經滿布泥炭沼地的巴伐利亞眾多地區之一長大的人。
一七五○年,數百年來形成的一片片廣大泥炭沼澤高地,大致上仍維持原貌,尚未有道路或運河縱橫其上,亦未為耕作農業所使用。只有少數地方的外觀因為採收泥炭而開始改變,其餘多數地方,仍讓人望而生畏。一直要到泥炭沼澤開始消失,有些德國人才開始視它們為「浪漫」。
我們的旅人若是往更高處爬,進入愛非山脈(Eifel)、梭爾蘭德(Sauerland)、哈次山脈(Harz)或厄爾士山脈(Erzgebirge)的高地,可能會看到另一個已經消失而讓人更為感傷的例子:數百座後來被水壩淹沒的山谷其中之一。其時,這些山谷的原野與村落尚未掩蓋於水面下,正如被水浸潤的高地泥沼尚未被原野與村落所覆蓋一樣。德國地貌有許多特色,永恆不變絕非其一。
工廠煙囪 鐵路以及蓬勃發展的城市
這本書所講述的,是德國人在過去二百五十年來如何改變他們地貌的故事,包括將草澤與泥沼改為新生地、將溼原排乾、將河流截彎取直,以及在高地山谷興建水壩。這些人為努力沒有一件是全然新穎的。
中世紀的熙篤會(Cistercian)修士曾排乾沼澤的水,而萊茵河第一次成功的「截彎」工程早在一三九一年。數百年前在德國的中部山脈甚至已經有某種水壩了,建造的目的是為了提供能源進行礦井排水──利用水來抽取水。一七五○年之後的水利工程與以往不同之處,在於其規模與影響之大。
這些工程對地貌的改變不亞於那些我們熟悉而顯而易見的現代象徵:工廠煙囪、鐵路,以及蓬勃發展的城市。為什麼有這些工程,是誰決定的,產生了什麼後果?我關心的是這些問題。我將這本書命名為《征服自然》(The Conquest of Nature),是因為當時的人們便是這麼描述他們所為之事。他們的態度隨著年代而改變,從十八世紀充滿陽光的啟蒙時代樂觀精神,到十九世紀對科學與進步的衷心信仰,再到二十世紀對於所標誌的技術官僚感到自信。(一九○○年,水力發電被描述為由穿著白袍的男人創造的乾淨現代能源,這些美好的描述現在讀來,一如六十年後的人們對核能發電的熱情期待。)在數十種大同小異的論調中,不變的是基本觀念:自然是我們的對手,必須被束縛、馴化、壓制、征服……諸如此類。
「讓我們學會對自然而不是我們的同類宣戰。」這是蘇格蘭作家詹姆斯.鄧巴爾(James Dunbar)在一七八○年所寫的,他認為人類應該對自然發起一場正當的戰爭,這樣的觀點在其後超過二百年的德國歷史中成為一再被提起的熟悉論調。
與鄧巴爾同時代的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of Prussia),其排乾過的草澤與泥沼比同期任何一位統治者都多,他曾在俯視奧得河(Oder)草澤新生地後宣告:「我在這裡和平征服了一個新省份。」十九世紀,思想進步的人追求的是建立在沼澤原上的聚落與蒸汽船的通航。
讓人類成為地球主宰者的特質之一
在自然科學的黃金年代,人類對自然的掌控被視為人類道德進步的標誌,那正是戰爭的反面。這樣的態度一直持續到慘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在許多評論者眼中,那場戰爭中斷了人類進程的自然軌跡。佛洛伊德在一九一五年寫下《對戰爭與死亡時期的思考》(Thoughts for the Times on War and Death),認為因為戰爭而「幻滅」(disillusionment)的事物之一,是認為人類衝突可以和平解決的這種信念,而此信念是受到「我們在掌控自然上的技術進展」所助長,因為,秩序與法律的文明價值是「讓人類成為地球主宰者的特質之一。」
戰後,馬克思主義文化評論者班雅明也提出近似的觀點,他感嘆:「取代了將水流自河川排出,社會將人流導向了戰壕。」(instead of draining rivers, society directs a human stream into a bed of trenches)談及水利工程時,這種化軍刀為犁刀的樂觀主義一直到二十世紀中期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仍是自由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的共同論調。
史實又是另一回事。太多時候,將沼澤排乾或讓河道轉向並不如我們所以為的是「在道德上等同戰爭」(借用實用主義代表人物威廉.詹姆斯的用語),而是戰爭的副產品,甚至是為戰爭服務。以腓特烈大帝的諸多土地改造計畫為例,沼澤排乾後,消除了逃兵藏身的陰暗角落,也不再阻礙腓特烈如戰爭機器的部隊行軍的路線。挖掘運河與壕溝的是士兵,管理移墾者聚落的是從前的軍隊供應商;而對自然的征服,往往是在以征服所奪取的土地上進行。
或者換個例子,看看十九世紀「導正」萊茵河的計畫。如果不是拿破崙毀滅了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讓德國的政治版圖變得單純,從而為改造這條河流開了大門,這個史無前例的龐大計畫不會在那個時候、以那種方式發生。類似的例子俯拾皆是。
普魯士的工程師和數以千計的工人為什麼要與北海(North Sea)和雅德灣(Jade Bay)瘧疾橫行的泥灘搏鬥十年?這是為了替普魯士與後來的德國艦隊建造一座深水港。為什麼排乾並墾殖沼原的腳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加快了?因為德國人在《凡爾賽條約》簽署後,自視為「沒有生存空間的民族」(Volk ohne Raum),因此每一畝耕地都重要。國家社會主義黨(即納粹黨)在為下一場戰爭做準備時,進一步發展了爭取食物的戰鬥,同時也是對自然的戰鬥。
他們在一九三九年之後為東歐規畫的水利計畫,則結合了技術官僚的自負,以及對他們所征服的「失序」土地上那些民族的輕蔑。種族、土地改造與種族屠殺,緊緊交纏。
歷代德國人所說的征服自然,換一個軍事隱喻也能貼切表達,也就是一連串的水的戰爭。在德國國內與海外都如此。水可以滿足許許多多人類用途。光是河流就提供了飲用水以及洗滌和沐浴用水。河流不僅灌溉作物,也透過魚類直接提供卡路里熱量。
被蒸汽船逼出河道的小船夫
它們帶走廢物,也提供運輸方式(十七世紀法國哲學家、科學家暨數學家布萊茲.帕斯卡〔Blaise Pascal〕曾說,河流是會移動的道路)。河流提供了冷卻用水與其他工業程序用水。河流驅動簡易的水車與複雜的渦輪,是人類歷史上真正「重新發明輪子」的例子。利用河流的這許多方式中,有些可以兼容並存,有些則否。本書中描述的德國水文改造,不管是將河流改道或開溝排水、排乾沼澤、挖掘運河或建造堤壩,每一項都讓這些分別用不同方式使用河流的人產生對立。
河流與溼地經過改造以服務新的利益方時,斷裂紛爭就出現了。早年,衝突往往存在於漁業或狩獵與農業之間,後來存在於農業與工業之間,更晚近則在兩個有權有勢的現代利益團體之間(如內陸航運和水力發電)。幾乎總有地方上或小規模的訴求與較大利益之間的某種衝突發生;最後也幾乎總是較大陣營占上風。正如德國首屈一指的水壩專家所說:「能夠掌控水之後,隨之而來的便是因水而發生衝突的機會。」
能夠掌控水,仰賴的是現代知識形式:地圖、圖表、清單、科學理論以及水力工程師的專業。對水的掌控也是政治力量的指標。德國地貌的改造是以脅迫的方式所為,而德國水戰爭的暴力面有時昭然若揭。沼澤地的漁村曾反抗遷離;被蒸汽船逼出河道的小船夫亦然。迎戰他們的是軍隊。
公然的暴力在十九世紀中期之後逐漸減少(只有德國人在整頓別人的水道時例外),國內的水戰爭移至法庭、國會和內閣部長辦公室上演。但是法國人所說的「軟強迫」(violence douce)一直隱隱存在。只要看看德國的水道是怎麼改造的,就能看見權力的界線如何分布。人類對自然的主宰,透露了有關「人類主宰」這件事本身的許多訊息。
不過,這本書訴說的不只是暴力脅迫的故事,也是同心一意的故事。不管為一條運河或水壩所起的爭議有多激烈——誰該出錢、誰將獲益——德國水體可被任意重塑的這個基本原則,在出奇漫長的一段時間內,一直是政客、遊說者、官員與意見領袖的共識。
可以重塑,也應該重塑。這種觀點不是菁英人士所獨有。許多人後來視掌控自然為自然的事情——或者如我們所說是「第二天性」。大眾熱情支持改造了土地形貌的偉大土木工程建設;河道治理或水壩竣工後,歡樂的啟用儀式上有許多致詞演說;著名工程師如尤翰.圖拉(Johann Tulla)和奧托.因茲(Otto Intze)享有十分崇高的地位;而大量流通的家庭雜誌在報導人類巧思的成果時那種興奮語調,都在在證明了這種態度。提倡水力發電的雅各布.辛斯麥斯特(Jakob Zinssmeister)醫師在一九○九年寫道「畢竟人類存在是為了主宰自然而非服務自然」,只是陳述了多數人的想法。
經常有人說,比諸英國人或法國人,現代德國人對於「現代性」的接受度較低,比較不世俗與物質化,對於機械文明懷抱更多敵意。這是被用以解釋國家社會主義為何吸引人的一個說法。如果你相信這種說法,我希望這本書會讓你再想一想。(全文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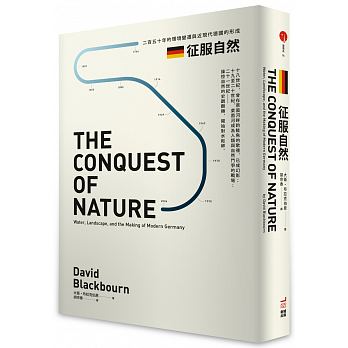 ※本文摘自《征服自然:二百五十年的環境變遷與近現代德國的形成》一書引言-德國歷史中的自然與地貌。作者為哈佛大學柯立芝歷史講座教授(Coolidge Professor of History),他於2007年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
※本文摘自《征服自然:二百五十年的環境變遷與近現代德國的形成》一書引言-德國歷史中的自然與地貌。作者為哈佛大學柯立芝歷史講座教授(Coolidge Professor of History),他於2007年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