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布林肯會王毅 中美達5點共識將舉行首場AI對話會議 2024-04-26 22:00
- 最新消息 徐巧芯婆婆一房3貸遭疑關說 台北富邦聲明:無超貸或特別處理 2024-04-26 21:40
- 最新消息 威尼斯徵收入城費首日亂象叢生 民眾示威抗議 2024-04-26 21:30
- 最新消息 國寶級水墨畫宗師歐豪年辭世 享耆壽90歲 2024-04-26 21:10
- 最新消息 布林肯記者會:美中關係明顯改善 美表達關切台海緊張局勢 2024-04-26 21:00
- 最新消息 投書:將拜媽祖的外在形式內化為自省功夫 2024-04-26 21:00
- 最新消息 雨神發威!中南部防豪大雨 雨勢延續至下周全台溼答答 2024-04-26 20:31
- 最新消息 花蓮慈濟醫師賞鯨離奇失蹤 船上留下背包人卻消失 2024-04-26 19:53
- 最新消息 【內幕】媒體認知偏離綠營價值 內定NCC主委劉柏立遭府院急撤換 2024-04-26 19:50
- 最新消息 德國逮捕4名中國間諜嫌犯 陸外交部:純屬無中生有 2024-04-26 19:39

兩位作者支持向有錢人課徵財富稅,並探討政府可以如何展開國際合作,向企業聯合課稅。(湯森路透)
第六章
阻止租稅競爭
二○一九年,國際貨幣基金要求一組專家就企業稅制與租稅競爭的未來發展提供他們的看法。參與這項問卷調查的多數專家回覆,在可預見的未來,租稅競爭「可能會更白熱化」。由於每一個國家都擁有自主選擇其稅制形式的主權,所以,沒有人有能力強迫租稅天堂停止它們的財政傾銷行為。因此,這些專家一致認為,只要還有利可圖,某些國家絕對不會停止以低於鄰國的稅率來吸引人,而可移動的盈餘也一定會設法尋覓最低租稅負擔的地點。當然,過度濫用租稅競爭文化所造成的問題並非全無解方,不過有些人認為,由於全球經濟的整合度已愈來愈高,未來最好別妄想對跨國企業課徵高稅率,因為那我們認為這個觀點是錯誤的。全球化的所有要素都不要求廢除企業稅。要不要消滅企業稅,選擇權操之在我。今日如火如荼的租稅逐底競爭是我們集體做出的決定所造成,或許那不是一個徹底自覺的狀態下做出的決定,也不是一個昭告天下般的公開決定,更不是一個經由透明且民主的辯論而做出的決定,但無論怎麼說,這都是一個選擇。我們大可以選擇協同各國的腳步,但我們卻沒有選擇那麼做。我們大可以選擇設法防止跨國企業在低租稅地點認列盈餘,但我們卻放任那些企業這麼做。總之,我們可以做出其他選擇,就算從今天開始也不算太遲。
為何各國無法協同合作?
為了釐清要如何擺脫目前的困境,必須先了解為何到目前為止,我們遲遲無法解決全球化所帶來的財政挑戰。
首先,這個問題有很多相對良性與時勢使然的解釋。金融全球化是近年來才形成的現象。目前世界上有接近二○%的企業盈餘是來自企業總部所在國以外的地方。但在二○○○年代以前,那個數字還不到五%;由於當時相關的金額並不算高,所以,這些盈餘是否被課徵適當的租稅,對國庫來說並不是那麼重要,因此也很少人─包括學術界與政策圈─在意這個問題。那就是跨國盈餘的遽增導致很多人措手不及的原因。當時各國的財政部會自始至終都假設一九二○年代的那個移轉訂價系統能繼續實現原訂目的。誠如我們在前一章討論的,這個假設太過樂觀。而因那樣的思維,過去鮮少人思考有什麼系統能取代這個移轉訂價系統。由於各方對此漫無頭緒,才會讓企業得以在幾乎免受懲罰的情況下,大肆利用法律上的缺陷圖利。

另外,要釐清企業的非法避稅規模,是一件曠日廢時的工作,原因很簡單,跨國企業的活動並不透明。當局通常不要求企業公開揭露它們在哪些國家認列它們的盈餘。蘋果公司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申報的年報中,只提供該公司的全球合併盈餘資訊,換言之,總部設於庫比蒂諾(Cupertino)的這一家巨型企業,並未公開揭露它在何處認列這些盈餘,即分別有多少盈餘是認列到它的愛爾蘭(並因此被愛爾蘭課稅)、德國或澤西島(Jersey)的子公司。一般大眾無從得知蘋果公司將多少資金移轉到租稅天堂,也無從得知其他巨型跨國企業的情況。
然而,無知也是顯而易見的罪魁禍首之一。就算沒有更多資訊來源或特殊的智慧,也能理解企業稅稅率為何劇烈降低。不過,除了單純的無知,我們做出那些選擇的理由當中,還有一些不是那麼良性的理由。
其中之一是,組成非法避稅集團的複雜勢力,成功遊說政策制訂者做出這個選擇。移轉訂價產業端賴一九二○年代設置的企業稅制為生:所以,保護這個稅制對這個產業而言可謂攸關重大。舉個例子,如果當局選擇不逐一向企業的子公司課稅,而是以一個合併實體的模式來向企業課稅,就沒有理由計算子公司之間的交易價格,在那種情況下,移轉訂價產業將在一夜之間被淘汰。這牽涉到極巨大的利害關係:如今在私人企業擔任移轉訂價專業人員職務的人高達二十五萬名,有些隸屬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有些則是直接隸屬跨國企業的員工。 若單純將他們視為被動的局外人,未免也太過天真,畢竟政策的設定攸關這些人的生計來源(譯注:避稅產業)的存亡。
非法避稅產業也卯足全力設法確保國際間盡可能不要採取協同的行動,因為它是各國不採取協同行動的既得利益者。畢竟若所有國家都採用一致的稅率,企業就不會在乎是否要將盈餘從某一地移轉到另一地,沒有理由將某個子公司的專利轉移到另一家子公司,也沒有理由向盧森堡的關係企業借錢。百慕達的企業稅政策對整個世界而言固然像一種劇毒,但對普華永道來說,那卻是大大的恩惠。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希望你相信租稅競爭是不可避免的,或甚至有好處─或兩者兼具。但真相是:若沒有租稅競爭,他們的業務將大幅減少。非法避稅產業向來以「租稅競爭是好事」的說詞來合理化他們的遊說活動;他們主張,若沒有租稅競爭,政府就會過於坐大。根據這個世界觀─政治科學家喬福瑞. 布瑞南(Geoffrey Brennan) 與經濟學家詹姆斯. 布坎南(James Buchanan)等人都為這個觀點辯護─透過民主方式選出的多數人代表,將對財產的所有權人課徵過高的稅賦,屆時這些財產所有權人將成為「多數人的暴政」下的受害者。而為防範這樣的風險,政府必須接受強大的約束,例如經由國際競爭而產生的約束力。這個概念和知識分子長期以來尋求經由一些非民主(nondemocratic)機構(例如憲法規定與法院)來剝奪民主的傳統不謀而合,尤其針對民主的財產監理規定。
本質上,「徵收租稅的權力必須接受制衡」的概念絕不荒謬。租稅政策該怎麼設計才正確?這是一個可以開放辯論的問題,但憲法與法律約束是設計租稅政策時絕對必須置入的要素。然而,「租稅競爭是好事一樁」的觀點,導致有錢人對民主的不信任上升到一個新境界:他們認為就算有法院、憲法與制衡制度也不夠,唯有百慕達才能保護他們免於受「多數人的暴政」的傷害,並幫助他們馴服利維坦巨獸(Leviathan,譯注:指國家權威);因為即使是崇高不可侵犯的憲法規定,都可能無法充分保障個人的財產。根據這個觀點,若涉及稅制,民眾沒有能力理性自我管理。
雖然我們難免企圖將這個理論貶抑為某種邊緣化的自由主義幻想和美國人特有的怪癖,但低估這個理論很可能是錯誤的。因為這個意識形態已在美國及其他地方留下深刻的印記,包括歐盟。歐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歐盟最接近憲法的一套規定─規定,除非所有成員國全體一致同意,否則不能採納共同租稅政策,而這項規定實際上已使租稅競爭變得根深蒂固。任何一個國家,無論是多小的國家,都足以妨礙歐盟內部所有促進稅率一致化的作為。換言之,諸如盧森堡(人口僅六十萬)等小國的意願,足以凌駕在五億歐洲人的意願之上。由於歐洲小國與大國之間的經濟利益分歧(較小的國家有極大籌碼可在租稅競爭中勝出),所以這項規定形同阻礙任何形式的租稅協同。儘管各方鮮少昭告天下般地公開陳述,但這項規定的根本理論基礎似乎是:歐洲的福利國規模過大,需要租稅競爭來促使這些國家變得節約一些。根據這個世界觀,民主無法完成這件任務。即使是煞費苦心的後民主(post-democratic,譯注: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導致議會角色衰退與主權喪失等現象)歐洲機構(歐洲委員會的非民選、無黨派的公正政策制訂者)都將無力控制社會支出。義大利需要馬爾他才能更節儉一些;法國需要盧森堡,而希臘則需要賽普勒斯。
但在現實世界,租稅競爭造成的代價遠遠超過一般所假設的租稅競爭利益。誠如我們先前討論的,若沒有足夠高的企業稅,就不可能實現累進所得稅,因為有錢人會趁著企業稅稅率很低時變形為企業,從而將所得稅轉化為(幾乎難以強制執行的)消費稅。而若無累進所得稅,幾乎就不可能解決不平等情勢的惡化。當然還有一系列的政策能幫助減輕不平等的程度,包括提高最低工資,乃至改革企業的公司治理、讓民眾更能平等地接受較高等教育、改善智慧財產的監理,以及遏制金融產業的不節制等。不過,在歷史上,累進所得稅一向是遏制財富集中化的最有效工具。
作為民族,作為彼此息息相關的國家,我們目前正站在一個抉擇點。若放任租稅競爭持續發展,租稅不公不義將更形惡化,不平等的情勢也會加劇。幸好我們還有其他同樣可行的途徑。阻止租稅競爭的急遽惡化是可能的:期待大型跨國企業在可預見的短期內乖乖配合繳納合宜的稅款並非空想。一個有效的行動計畫必須具備四個支柱:樹立典範(exemplarity)、協同、防禦對策,以及對搭便車者的懲罰等。
***
國際協同刻不容緩!
值此時刻,你可能想知道,如果大國真的開始善盡管轄本國跨國企業的責任,並開始扮演「最後租稅徵收者」,將會發生什麼事。到時候,難道飛雅特、蘋果和和萊雅公司不會將總部遷移到租稅天堂嗎?幸好解決這個威脅的方法不只一個,其中,最重要的方法是透過國際協同。誠如我們先前討論的,多數國家早已同意調整法律,以一致性的規定來限制最膽大妄為的盈餘移轉行為。顯而易見的,下一步是由各國達成共同最低租稅協議: 二十大工業國(G20,它包含世界上所有最大型的經濟體)可以全體同意對本國的跨國企業─無論其營運活動在何處發生─課徵二五%的最低稅率。畢竟這些國家已經掌握了開徵這項最低稅賦的資訊,而且,由各國扮演租稅最後徵收者,也符合各自的國家利益。說來或許有點奇怪,儘管近幾年租稅競爭愈來愈白熱化,但解決方案其實近在眼前。
但G20 共同認可的最低稅賦將無法解決所有問題。企業依舊能將企業總部遷移到租稅天堂,以達到非法避稅的目的。這個議題已漸漸成為公共辯論領域的重要話題。以美國來說,「稅賦倒置」(tax inversion)的幽靈(美國企業與愛爾蘭或其他低租稅地點的外國企業合併),正陰魂不散地糾纏著各國的政策制訂者。
不過這個危險被誇大了。儘管租稅倒置的話題不斷,實際上卻鮮少企業真的將總部遷移到熱帶島嶼。不可否認,過去有一些挺高調的案例:埃哲森諮詢公司(Accenture)在二○○一年從芝加哥倒置到百慕達(後來又搬遷到愛爾蘭);財務顧問公司拉札德(Lazard)在二○○五年將紐約企業總部搬遷到百慕達;還有,膳食補充劑公司賀寶芙(Herbalife)從二○○二年起就是開曼群島的榮譽居民。根據彭博社(Bloomberg)所維護的逃稅追蹤器,一九八二年至二○一七年,共有八十五家美國企業放棄美國國籍(其中很多隸屬製藥產業部門,且多數企業多數鮮為人知)。除了上述企業,我們還可以加入幾家從成立後就將總部設在境外金融中心的企業(或是很久以前就搬遷),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或許是油田服務業巨擘斯倫貝謝公司(Schlumberger),它的總部設在南加勒比海的庫拉索島。
這些現象聽起來固然頗令人憂心,但若你體察到這些個案不過只是滄海中的一粟,就不會那麼恐慌。目前世界前兩千大企業當中,只有十八家企業的總部設在愛爾蘭,十三家設在新加坡,七家位於盧森堡,還有四家設在百慕達。依然有接近一千家企業的總部是位於美國和歐盟,而剩下的多數大企業的總部則是設在中國、日本、南韓以及其他G20 國家。
儘管誘因非常多,卻只有少數企業倒置,根本的原因或許是企業的國籍不容易操縱。企業國籍的定義受嚴謹的規定約束。舉個例子,一旦某企業在美國設立登記,它就不能將總部遷移到海外:就算是將總部遷移到海外的美國企業,美國政府還是會基於租稅目的,將之視為美國企業。唯有被外國收購,美國企業才能改變其國籍;換言之,唯有和外國企業合併,美國企業的國籍才可能改變。而且要構成合法有效的倒置,相關的合併案件還必須符合特定條件,且這些條件隨著時間而變得愈來愈嚴格,尤其是二○一六年歐巴馬總統仍在位時。最重要的是,企業的所有權必須產生意義重大的實質變化才能轉換國籍:就算一家美國企業和位於茫茫大西洋上的某百慕達空殼公司合併,它也不能成為百慕達籍企業。所以實務上來說,美國企業巨擘根本不可能搬遷到加勒比海的無人小島。從歐巴馬訂定監理規定後(目前為止,川普還保留這些規定),企業已經完全停止稅賦倒置行徑。
第二個關鍵的教誨是:即使是只有少數幾個大國參與的國際協同,還是有可能遏制非法避稅行為。如果G20國家明天開始對本國的跨國企業課徵二五%的最低稅率,世界上就有九○%以上的盈餘會隨即被課徵二五%以上的有效稅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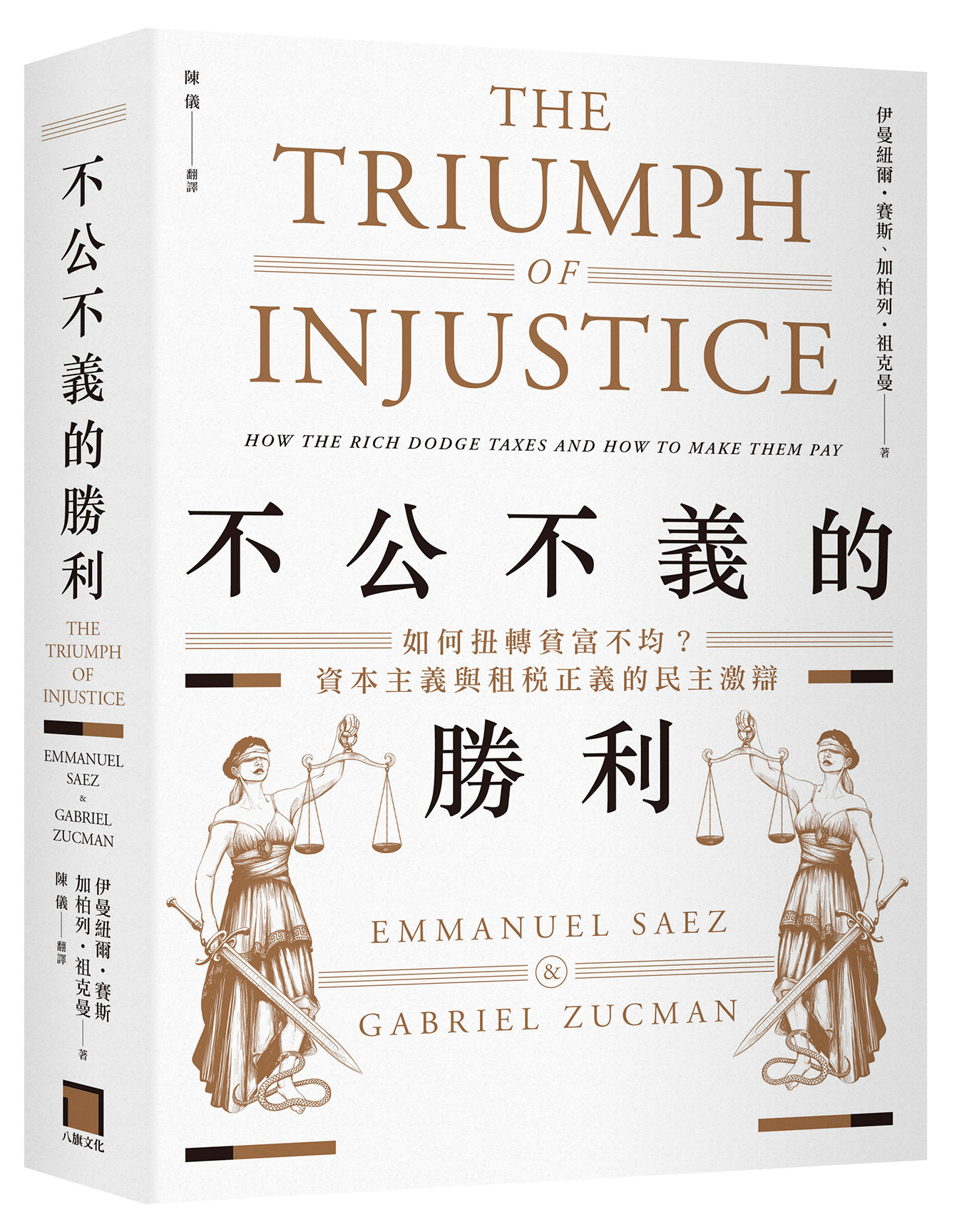
作者:
伊曼紐爾・賽斯( Emmanuel Saez)
加州柏克萊大學經濟學教授、公平發展中心主持人,世界不平等實驗室協同主持人,曾獲克拉克獎章及麥克阿瑟獎。與皮凱提合著《租稅革命:二十一世紀的所得稅》。
加柏列・祖克曼(Gabriel Zucman)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助理教授、加州柏克萊大學的研究員,正巧在全球陷入2008以來金融海嘯的時候開啟其學術研究生涯,被法國《世界日報》譽為「新潮流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師承法國知名經濟學者、《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兩人長年致力於研究全球財富分配議題,引領注重實務與應用的經濟學新趨勢。祖克曼被媒體形容為「財富偵探」,他的專長是找出超級富豪們藏匿在避稅天堂的財富,並設計出一套向富豪課稅的方法。著有《富稅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