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寶林中毒案累計3死 40歲馬籍男子裝葉克膜搶救1個月仍離世 2024-04-27 16:27
- 最新消息 趙麗穎《與鳳行》熱戀林更新CP感炸裂 粉絲為兩人求愛情鎖他冷回「這4字」全網炸鍋 2024-04-27 16:26
- 最新消息 看到必拿!《聯盟戰棋》14.8b裝備排行:最強五大顎爾神器&輔助道具! 2024-04-27 16:00
- 最新消息 國民黨立委剛啟程訪中 解放軍派22架次軍機擾台 2024-04-27 15:55
- 最新消息 【本周最終回】《淚之女王》紅到連孫藝真都在追 最強綠葉郭東延竟是金智媛「前男友」 2024-04-27 15:26
- 最新消息 NCC委員提名防綠化 藍營提案修法「依政黨比例任命」 2024-04-27 15:22
- 最新消息 猴硐貓村越夜越可愛!貓公所籌備處換新裝、室內增設除濕機 為貓咪打造舒適環境 2024-04-27 15:00
- 最新消息 國防部發言人孫立方7月提前退伍 將與部長邱國正共進退 2024-04-27 14:49
- 最新消息 別樂觀!全台14座水庫蓄水率僅2、3成 仍需雨神續命補水 2024-04-27 14:11
- 最新消息 秦昊《哈爾濱一九四四》熱度超越楊紫《承歡記》奪冠 他分飾兩角狂瘦12公斤內幕曝光 2024-04-27 13:33

台灣近代史近乎泥沼,其中摸爬滾打、忽鄙忽亢的「水仔」(吳慷仁絕佳演繹)才是它最真實貼切的隱喻吧!(公視提供)
《斯卡羅》是這個月的觀影熱點,評論兩極,不但台灣如此,連對岸的影迷和小粉紅都盯上了,不惜網路上一戰。
官方資料如此清晰:《斯卡羅》改編自陳耀昌小說《傀儡花》,事件取材自台灣真實發生過的歷史事件。1867年,美國商船「羅妹號」在臺灣恆春半島發生船難,他們登島求助時,卻遭當地原住民誤殺,造成「羅妹號事件」。後來美國派軍隊攻打恆春半島原住民,然而擁有現代武器的美軍,卻不敵當地原住民,帶隊軍官反遭原住民擊斃。事後美軍派領事李仙得來台調查,當時除了有在地原住民、平埔族及閩、客庄人,清廷、外國各股勢力都在台灣匯集,衝突一觸即發。
但實際上歷史與劇集都不可能這樣兩三句話概括。可以說,《斯卡羅》是一部非常困難的作品。不只是拍攝技術的困難,這點《斯卡羅》最完美地克服了,目前聽到最多的讚譽是:這不像一部台灣電視劇,甚至超越多數韓劇和陸劇,達到Netflix高質素劇集的水準。
毫無疑問,《斯卡羅》的攝影、美工和影視語言,都超乎水準地還原了我們所能想像的歷史細節。甚至最被人挑刺的政治立場,隨著劇集的展開(目前播到第四集),依然有開放的可能性。備受爭議的美國領事、日後的日本侵台顧問李仙得的刻畫還不至於臉譜化,這就是本片吸引我繼續看下去的一個原因。

但編劇最堪憂,一方面是那個時期的台灣歷史本身的確過分地複雜,各種力量的交纏是曖昧甚至茫昧的,如果非要用現在流行的「身份認同」、「地緣政治」等概念去評判一百多年前的先民、組織他們的關係,注定是錯位的——偏偏目前劇情裡最刺眼的,就是片裡的「文明人」總是把對話提升到非常「上綱上線」的地步,感覺是——「請回答我,1867!」——可是1867年的台灣住民,怎麼可能從屬2021年的種種糾纏。
另外,最難拍的電影就是每一個角色都有他自私的理由的電影,《斯卡羅》裡每個人都是「好人」,因為他們為自己與族人的生存而搏鬥;但每個人也都是壞人,因為他們視非我族類為草芥。漸漸地,《斯卡羅》朝著這個方向前進,劇情要保留那種繁雜莫辨的原生狀態的話,觀眾會失望;但使用好萊塢式戲劇衝突來引向大團圓結局嗎?歷史會失望。
不要問李仙得畢麒麟是好人壞人?原住民大股頭二股頭是好人壞人?柴城力保社寮頭人是好人壞人?其實,只有單純的蝶妹會用好人壞人去區分她剛剛遇上的人。如果回歸蝶妹視角,也許《斯卡羅》會真實很多,但前提是蝶妹需要更早確立她的自覺和力量,對於編劇來說,這是難說通的地方,因為歷史上原本沒有這樣一個掙扎在身份認同甚至性別覺悟上的卑微角色,她是創作者的主觀意志塑造的一個「典型」——或者一不小心就淪為理念的「載體」了。
當然,歷史、文學和影視作品,這三者還是需要一個清晰的區分,不能拿其中一個去完全凌駕另外兩個型態。如果可以多少飄離歷史的桎梏,《斯卡羅》會是一個優秀的作品(除了還要修訂許多文藝邏輯上的小硬傷)。關於身份之辯,也有弦外之音動人的暗示,比如李仙得強調問蝶妹記得媽媽的歌、回家的路嗎,看起來很生硬和煽情,但實際上是因為他不記得了媽媽的歌和自己回家的路了——這樣看一個矛盾叢生的歷史人物,也許會多幾分悲憫。
但創作很難在各個方面都能如此超越歷史,因為台灣近代史近乎泥沼,其中摸爬滾打、忽鄙忽亢的「水仔」(吳慷仁絕佳演繹)才是它最真實貼切的隱喻吧!且讓我們拭目以待餘下的劇情,看看作為「台灣本我」的卓杞篤、作為「台灣自我」的水仔、作為「台灣超我」的蝶妹姐弟,將會如何完成自己的敘事。我也將再度嘗試評論——儘管評論也如此困難。
 《斯卡羅》的攝影、美工和影視語言,都超乎水準地還原了我們所能想像的歷史細節。(公視提供)
《斯卡羅》的攝影、美工和影視語言,都超乎水準地還原了我們所能想像的歷史細節。(公視提供)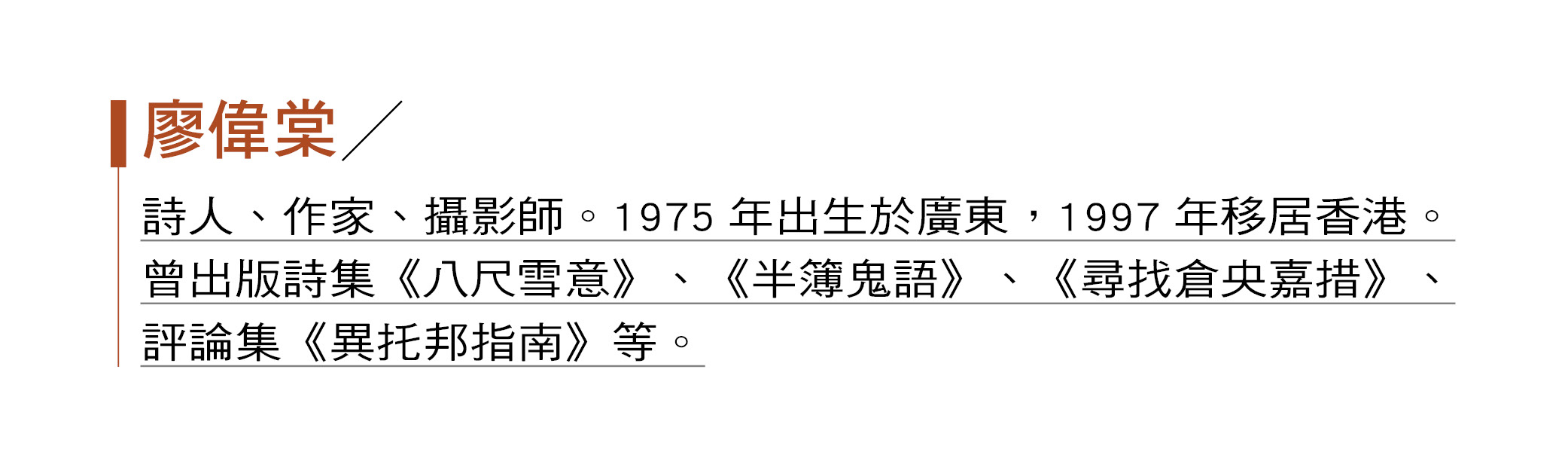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吳磊哭哭】趙露思與張藝興現身新疆爆熱戀 3大證據被抓包全網沸騰
- 麥當勞買一送一!10 塊麥克雞塊、薯餅、焦糖奶茶通通有 歡樂送買一送一、深夜食堂享 79 折
- 成毅新劇虐戀李一桐預告曝光400萬人爭睹 他白髮揮舞火劍帥度超越《蓮花樓》
- 大雨狂炸補水!曾文水庫降雨達18毫米 南化水庫7小時進帳逾4萬噸
- 白敬亭、章若楠演《偷偷藏不住》姐妹作 兩人甜摟畫面曝光3敗筆被嘲「情侶變父女」
- 肖戰新劇搭檔《惜花芷》張婧儀3大高甜名場面搶先看 兩人夜會甜蜜相擁CP感爆棚
- 楊紫《長相思》虐戀檀健次、鄧為掀淚海 第二季張晚意冷血復仇埋悲劇結局
- 《春色寄情人》李現、周雨彤CP感爆棚收視狂飆 兩人戲外被喊「在一起」竟都羞紅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