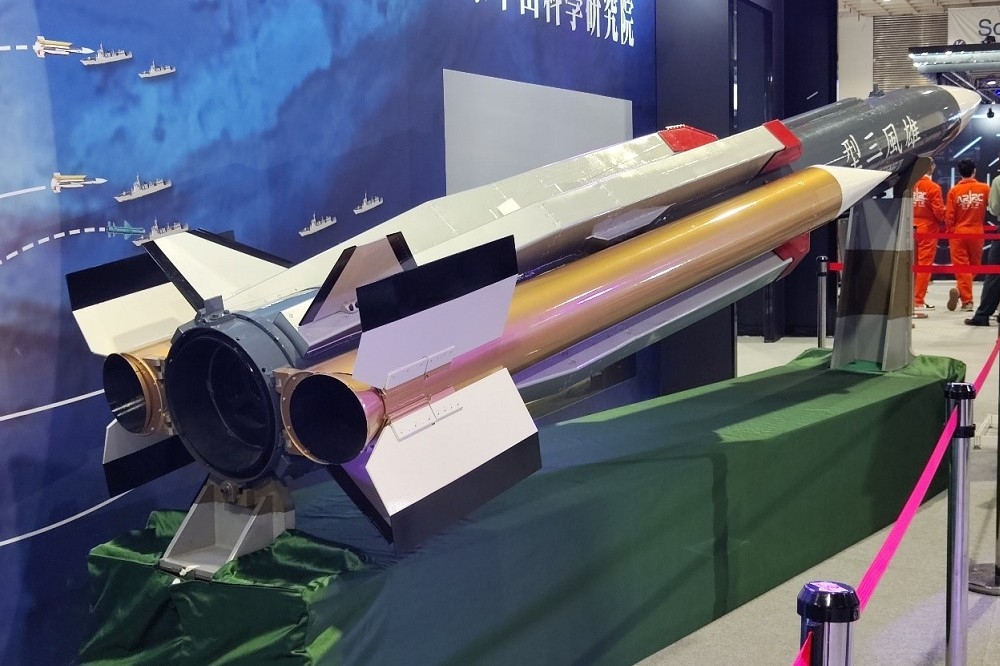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提升M1A2T戰車夜戰效能 陸軍規劃夜視系統擴及駕駛員 2024-04-28 18:45
- 最新消息 【一周天氣預報】又有鋒面來襲!明高溫上看36度 周三起迎大雨 2024-04-28 18:45
- 最新消息 高雄漢來自助餐增至46人餐後腹瀉 疑生熟食混用停業清消 2024-04-28 18:41
- 最新消息 嘉義虎媽失控飆罵「要女兒下跪」 少女裸雙膝當街苦跪6分鐘原因曝 2024-04-28 18:06
- 最新消息 中橫宜蘭支線台7甲南山村路段提前搶通 夜間預警封閉 2024-04-28 18:01
- 最新消息 台東部落傳槍響!53歲男疑久病厭世 「腹部中彈」倒家門前亡 2024-04-28 17:51
- 最新消息 NCC舉《憲法》拒提供鏡電視資料 藍白轟公然挑釁:是不是心中有鬼? 2024-04-28 17:42
- 最新消息 【有片】鐵達尼號文物「金懷錶」破紀錄天價落槌 世界富豪送孕妻上救生艇後罹難 2024-04-28 17:10
- 最新消息 肖戰新劇搭檔《惜花芷》張婧儀受虐濺血造型曝光 他上戲前「這表情」萌翻全網 2024-04-28 16:40
- 最新消息 《不夠善良的我們》許瑋甯裸身告白柯震東掀淚海 賀軍翔這句話斬舊情全網鼻酸 2024-04-28 15:25

在如何詮釋當代人類境遇的命題上,中國仍需要從「亞非拉」走進歐美;歐美各國尚掌握工業革命至今的物質文明發展脈絡和今日資訊革命的各項生產資質。(湯森路透)
2019年底的新冠肺炎發生至今,國際各界對中國有著不同的討論意見,作為國際上最大的政府間衛生機構,也是聯合國的專門機構,世界衛生組織也成為中美兩國權力競逐和爭取疫情詮釋權的場域。美國作為目前確診人數最高的國家,其身分又為當前國際體系的唯一超強,影響所及不只是國際關係的全球霸權地位,更是西方文明是否能詮釋當代人類命運境遇的路口。
中美關係轉向有其軌跡
當歐美日等高度發展地區疫情失控之際,以美國為首興起對中國的問責聲浪,然而以疫情作為事由並非一日之寒,而是自2001年克林頓卸任總統以來,中美關係一路由友好走向競逐的破口。克林頓政府時期的對華政策主軸是接觸(Engagement),從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將人權政策與經濟政策脫勾,到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每一步都在致力於將中國拉入國際體系,希望藉由經濟上走向資本主義的同時,促使中國內部逐漸發生結構性的改變,並認同西方文明的普世價值。
911世界發生後,小布希政府也需要中國協助其全球反恐的動作,雙方還算有一段不短的友好時期,在2002年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提及中國之處仍認為是在全球反恐合作的重要夥伴,但是提及中國的的次數已從2001年的58次下降到20次。但是在2005年9月21日,一個中美關係的新字眼重新定義中美關係:「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這是由時任副國務卿,且曾任貿易副代表的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基於中美貿易問題所出,雖然他與當時任財長的包爾森(Henry Merritt "Hank" Paulson)仍是對中國較為正面的態度,但是在2006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提及中國的次數為30次,因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更為現實的語境而多了一些疑慮。
歐巴馬時期已留有後手
歐巴馬時期的中美關係仍是較為正面穩健,在談及與中美關係時,用的大多是正面詞語,如「建設性」(constructive)、 「有效的」(effective)、和「里程碑」(landmark)等語境。然而,奧巴馬第二任總統時期,使用了「競爭」,「監視」等比較負面的字眼。歐巴馬延續包爾森的中美對話機制,在美國政界創造G2這種概念性的名詞,希望在攸關中美利益的議題中討論合作機制。
另一方面,歐巴馬也在2010年接見達賴,並且提出將價值64億美元的武器出售給我國,包括博勝案第二期高端的C4ISR系統(指揮、管控、通訊、電腦、情報、監測和偵察),對於我國國軍科技含量的提升和軍事事務革新有著相當關鍵的作用,其戰略意義不亞於F-16等軍機的出售,以及114枚愛國者三型(PAC-3) 飛彈和2套射擊模組與1套訓練模組,至今仍然有效的作為我國領空防衛重要的威懾力量。當時美國對於中國的防備之心已越來越深刻,2014年歐巴馬訪日本時還聲明《日美安保條約》包括包括尖閣諸島(即釣魚臺列嶼)在內,明顯對中國在東海謀求突穿第一島鏈造成牽制的作用,更於任內提出「亞太再平衡」(Rebalance)和太平洋支點(Pivot to Pacific)等針對中國的戰略構想,事實上已遠遠不同於同為共和黨的克林頓任內對中國的友善態度。

今日中美兩國在全球疫情和世界衛生組織上所呈現的態勢,並不是川普或習近平兩人互爭一時之快,而是美國知識界和各菁英階層對中國崛起的疑慮逐漸積累而成,而在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後,美國更逐漸遠離柯林頓時期將中國拉入現有國際體系的目標。而「一帶一路」也非是橫空出世,其主要涵蓋地區為亞非拉各地的發展中國家,其核心精神是上個世紀毛澤東「團結亞非拉」的延續,中間歷經鄧小平時期的「韜光養晦」、江澤民時期「向西走出去」和成立「上海合作組織」,到胡錦濤時期的「和諧發展」,都持續積極的對這些地區提供政策貸款、無償援助和低價軍售等各種形式的協助,只是未必體現於「一帶一路」這樣有具體語境的「陽謀」之下。
中國的國際秩序發軔於貧窮
當年毛澤東提出「團結亞非拉」之際,整個中國仍陷於貧窮和文革的負面影響之下,甚至需要以馬鈴薯等實務去償付與蘇聯的交易,但是中國卻持續對亞非拉各國提供資源與協助,特別是對非洲國家的支援。在1960年代非洲各國剛獨立時亟需要國際支持與認同,即使中國也正逢「大躍進」時期造成的饑荒也仍持續輸出糧食至非洲各國,這與當時中國不被聯合國和歐美主要國家所承認固然有關,但是也確實為中非關係奠定深厚的基礎。
時至今日的中非關係已成為中國在各個國際組織的重要基底,除了是「一帶一路」的核心發展區域之一,中非之間的貿易額也在2000年-2017年間從100億美元成長到2,000億美元,與此同時,非洲與歐美國家之間的貿易額則增長乏力。經貿的穩定成長與依賴,使得非洲國家大力幫助中國進入聯合國的各個組織。以人權理事會為例,2019年在新疆議題的較勁下,22個西方國家雖聯名譴責中國侵犯人權,但是有37個國家上書讚揚中國在新疆優異的反恐成果和對人權的維護。
中國從公共資源建立詮釋權
今日的中國還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聯合國預算第二大貢獻者,2019年貢獻了3.7億美元,佔聯合國總預算12%。在聯合國15個專門機構中,已有四個單位由中國擔任負責人,美國只有一位,使得中國有更大的權力提供公共財予「一帶一路」和非洲國家,甚至趁虛而入填補美國放棄的權力縫隙,進而滿足更多發展國家的需求。在西伐利亞體系下一國一票的平等原則下,中國所展現的是已有能力對國際秩序提出貢獻,並且藉由國際組織的參與宣傳期價值觀,而不是只有「大撒幣」和「大外宣」的粗暴形象,在美國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和《中程核飛彈條約》後,更使得西方文明逐漸失去詮釋當代文明價值的能力。
中國之所以能得到非洲國家的支持,不止是長期以來的援助,更是奠基於長期提供且逐漸擴大的各種公共財,中國近日提供世界衛生組織6億美元只是冰山一角。人民解放軍海軍在印度洋的亞丁灣護航雖然有其戰略目的,但也確實降低索馬利亞海盜的危害。中國目前提供聯合國維和部隊最多的人力,最近5年經常維持在2,500人左右,並且從人民解放軍中組織專門從事國際維和任務的8,000人常設部隊,還保證未來10年提供10億美元的聯合國維和任務費用。相對於西方霸權中國際秩序和自由之間的相互牴觸,學者石之瑜教授稱之的「共天下」是建構於秩序與自由之間相互支持的關係。

在中國「共天下」秩序,中國提供這些公共財不能迴避的目的是在非洲寶貴的石油和資源等利益,但是在地化的作為上卻也讓歐美各國難以追趕。江蘇省南通市的公安部門已在東非各國建立「警僑聯動」的機制,公安進入非洲國家的僑民社區進行協助的同時,也幫助當地社區打造治安體系,並提供中國公安系統的訓練和設備。軍事方面,知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吉布地保障基地」作為中國在非洲權力投射的存在,而中國的軍事軟實力也在非洲等國家深植,坦尚尼亞軍隊被稱為非洲的人民解放軍,其建置和設備都是基於人民解放軍的標準,上層軍官有一半以上曾至中國軍校進修,普遍會說流利中文,平時也緊追中國上層的思想,甚至對「仗在哪裡打,兵就到哪裡練」都能朗朗上口。這些深耕細作的成果早已超越銳實力(Shape Power)的層次,在非洲多數國家的政府與社會結構中形成脈絡的中國價值,非洲國家受到中國的支持能滿足自己的目的,也能維持中國期望的結構,這種國際秩序實在難以被一時的輿論風向所撼動。
川普任內加速卸除美國在國際體系扮演的角色和提供的各類公共財,時逢疫情盛行的「天下大亂」 之勢更給予中國趁虛而入的機遇,這正是北京面對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下最好的突破口。中國可能不需冒著軍事鬥爭風險,避免沿著「修習底德陷阱」發生大國衝突,但是在如何詮釋當代人類境遇的命題上,中國仍需要從「亞非拉」走進歐美。歐美各國尚掌握工業革命至今的物質文明發展脈絡和今日資訊革命的各項生產資質,中國如何在疫情之中以「形而上」詮釋當代文化與文明,中非關係的經驗是一種可能性,雖然仍不是普遍性。
小國若無文化 主體性難以為繼
台灣在這次世界衛生組織上的較勁中,作為美國為主的國際秩序的一份子,從社會輿論到實質的支持不遺餘力,同時也為台灣爭取寶貴的國際能見度,並從國際政治的事件中創造「再在地化」的機會,但對小國而言「扈從」和「抗衡」都不是最佳方案,也需要以文化同源的角度思考避險策略,如何在後疫情時代中應對一個以中國語境來詮釋的國際秩序,或者是所謂的「天下」。
回顧中美交鋒前沿的台灣,中國也以「以疫謀獨」的角度看待台灣當前在全球展現的各種舉措。中國對此是以「超軍事實力」作為回應:基於軍事而以文化、經濟或科技的形式展現的實力軍機繞台、漁船侵擾、抽取海底砂石。另一方面不只是提供經貿利益,更透過小說、影視、新媒體與網路遊戲影響玩家的言論和思想,使得特定個體或群體維持與中國的關係性,甚至再脈絡化,使得其生活世界持續以中國的語境詮釋而失去主體性。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台灣絲路文化協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