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檢方第9度提訊!被問不法所得是否上億 柯文哲未回應 2024-12-11 22:35
- 最新消息 【大法官人事案】難忘被害人家屬絕望神情 王碧芳:我支持死刑 2024-12-11 22:16
- 最新消息 法總理上任僅3個月垮台 馬克宏擬48小時內提新人選 2024-12-11 21:56
- 最新消息 動輒飆罵下屬「混蛋」 數發部2主管涉霸凌降調非主管職務 2024-12-11 21:51
- 最新消息 南韓總統辦公室僅提交小部分資料 警方搜查行動無功而返 2024-12-11 21:28
- 最新消息 陸委會「有條件」放行雙城論壇 北市府:秉持4原則持續交流 2024-12-11 21:14
- 最新消息 【大法官人事案】反對翁曉玲版《憲訴法》 王碧芳:會癱瘓憲法法庭 2024-12-11 20:45
- 最新消息 保護本土產業鏈 美將宣布中國太陽能板關稅提高2倍 2024-12-11 20:41
- 最新消息 「一隻阿圓」穩交陳百祥 眼尖網友:去年就曾一起去韓國! 2024-12-11 20:10
- 最新消息 「入冬最強冷氣團」來襲周末恐剩10°C 中醫推薦「2種養身飲」暖身又暖心 2024-12-11 19:42

1000x80_13.jpg)
保羅
• 杜克大學博士後副研究員
新的鍍金時代就在這裡。隨著富人和強國收集最先進的技術設備,普通工人越來越關注「自動化的上升趨勢」。
有關機器人不可避免的大規模流離失所將成為大量的素材。報告稱,技術性失業將加劇經濟不安全,使就業更加不穩定。雖然牛津大學經常引用的一項研究警告稱,47%的美國工作崗位有被機器人接管的風險,但麥肯錫公司告訴我們,這並不是那麼糟糕:只有1/3的工人會被機器取代。
然而,假設這種結果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完全錯誤的。從歷史上看,自動化創造的就業機會遠遠超過損失的,技術進步帶來了更高的工資,更長的預期壽命,更快的增長,就業增加以及危險和卑微的工作。
然而,在這個新的鍍金時代出現的電力不平衡挑戰了自動化與廣泛分享的利益間的長期聯繫。人們越來越擔心「過剩人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工作的未來是否會服務於許多人而不是少數人,這取決於機器人,這取決於我們。
技術水準仍低
許多評論家通過世界末日的鏡頭來看待21世紀的經濟。但至少對於經濟學家來說,任務是退後一步,做他們接受過訓練的事情:看看數據。
如果我們遇到自動化革命,我們會期望看到高飛的生產力數字,因為技術變革往往會轉化為來自相同數量,投入的更多產出,但數據描繪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畫面。
在1947年至1973年的戰後繁榮期間,美國經濟的生產率以每年2.7%的趨勢增長,2006年至2017年間僅為1.2%(實際上近年來的實際數據低於1%)。遠非技術革命,美國實際上處於勞動生產率增長緩慢的中期,這意味著技術變革水平較低。
正如新經濟思想研究所的透納(Adair Turner)所稱,經濟學家對這些趨勢感到困惑,因為關於快速自動化和微不足道的生產力增長的事蹟根本就沒有幫助。對他而言,透納對這一現象提供了幾種解釋。
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洛(Robert Solow)1987年著名的諷刺說,電腦出現「無處不在」,但在生產力統計數據中,資訊技術可能會產出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善人類福利。這似乎是顯而易見的,然而更簡單的解釋是自動化太少而不是太多。
除了生產力數據之外,投資數據也對美國經濟正在經歷或處於技術革命邊緣的主張產生懷疑。
正如經濟政策研究所的米歇爾(Lawrence Mishel)和雪賀姿(Heidi Shierholz)所表明的那樣,過去十年來美國的資本投資是一代人以來最低的,與前幾十年相比,對信息技術硬體和軟體的投資顯著下降。
自動化持續成長
儘管如此,即使沒有技術熱潮,自從工業革命以來,自動化仍將是經濟的一個持久特徵。新技術和生產方法將擾亂勞動力市場,工人將失去工作。等待我們的創造性破壞無疑會破壞社區,職業,甚至整個行業。歷史表明,勞動力替代自動化的短期和短期影響是真實存在的。
但是,今天和過去之間存在著重要的差異。
從歷史上看,技術進步與工人生活水平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十年裡,隨著新技術的採用,平均工人工資上升,並在20世紀70年代突然爆發。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權力的鐘擺已經以犧牲工人為代價,徹底轉向企業。
雖然技術在總體水平上繼續使經濟受益,但美國現在的歷史上存在高度不平等。這與一般的技術變革或特別是最近的技術變化幾乎沒有關係。改變的是如何分配這些好處。沒有經濟法規定工人在引入新創新時必須失敗。相反,經濟中的贏家和輸家是由管理它的規則和制度決定的。如果今天的資本對勞動力的權力比過去更多,那是因為公共政策的選擇,而不是技術。
例如,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恩承葛林(Barry Eichengreen)指出,為什麼美國公司「將他們的工人視為一次性零件,而不是投資於他們」,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現行的權力不平衡是由於事實上,「工人代表的董事會成員,強大的工會和政府對私營部門培訓的監管不是現行製度公式的一部分。」
需要做什麼
儘管自動化並未按照許多人認為的速度進行,但政策制定者仍必須解決其在美國政治經濟背景下對就業和不平等的影響。
正如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的斯基德爾斯基( Robert Skidelsky)所指出,技術失業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問題」,但自動化和人工智能(AI)帶來的威脅尤其值得關注,因為傳統的政策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斯基德爾斯基對自動化的反應是提出黃色警告標誌。「如果目標是盡可能地提升所有船隻,」他寫道,「然後全球化和自動化的一些放緩是不可避免的。」
同樣,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席勒(Robert J. Shiller)提出「適度稅收」的理由。關於機器人,「減緩顛覆性技術的採用,阻止自動化導致的不平等加劇。」
斯基德爾斯基和席勒對當前制度環境下自動化對就業和不平等的影響的擔憂是合理的。但是,為什麼不修改制度環境,而不是阻礙技術進步,以便技術變革再次有助於工人的福祉?
這就是美國在整個大西洋地區更具社會民主傾向的對手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例如,瑞典人已經開放擁抱自動化。正如瑞典就業與融合部長告訴《紐約時報》的,「工作崗位消失了,然後我們培訓人們從事新工作。我們不會保護工作。但是,我們將保護工人。」
毫無疑問,80%的瑞典人對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有正面看法。相比之下,72%的美國人擔心機器人會從事許多人類工作。
當然,與瑞典人不同,美國人有充分的理由擔心。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保護美國工人的社會契約一直在崩壞。為了幫助工人適應經濟變化,許多學者向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建議。例如,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皮薩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和布辛(Jacques Bughin)指出,「工作未來的辯論往往忽略了勞動力市場將如何演變以及改善或加劇已經嚴重的技能不匹配的問題在發達國家。」
因此,他們呼籲增加開支,不僅要培養工人的認知技能,還要培養「創造力和社交技能。」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經濟學家泰森(Laura Tyson)和新美國的孟東卡(Lenny Mendonca)都同意這一觀點。但是,不僅僅是增加支出,他們還希望「技能挑戰需要一場史詩般的工人學習和培訓改革......與一個世紀前建立普及中等教育相提並論。」
當然,很少有人反對擴大技能培訓的政策,這往往得到兩黨的支持。對工人如何獲得技能的重大調整 - 可能與德國的學徒計劃一致,當然似乎是有條不紊的。
追求領先
我們之前曾在美國進行過這些辯論。為了應對20世紀60年代人們對自動化的普遍擔憂,美國前總統詹森(Lyndon B. Johnson)曾委託編寫了一份關於「技術與美國經濟」的報告。
報告於1966年發布,承認除非美國採用正確的經濟規則,否則自動化可能會加劇失業和不平等。但它也指出,公共政策,而不是技術本身,應該成為自動化將為誰增加的辯論的中心,以及它將留下誰。
事實上,政策行動有時是故意不採取行動,才使美國走向了目前的狀態,一個極不平等的社會,數百萬工人擔心他們的工作和生計。好消息是,聰明的公共政策也可以讓美國走出困境。考慮到這一點,部分想法至少應該在檯面上進行辯論。
首先是充分就業的原則。
根據1946年的《就業法》(Employment Act of 1946)和1978年的《充分就業和平衡增長法》(Full Employment and Balanced Growth Act of 1978),美國政府有權追求「最大限度的就業」。這意味著美國聯準會(Fed)在制定貨幣政策時,也有雙重任務來實現就業目標及價格穩定。
然而,到目前為止,Fed幾乎完全由通貨膨脹指導,同時將「充分就業」定義為任何水平的就業恰好與該目標一致。
雖然現在是Fed認真對待全面就業任務的時候了,但僅憑這一點還不夠。為了消除非自願失業,美國政府還應該制定工作保障,政府將為所有想要的工作年齡的成年人提供就業機會。這正是詹森總統委員會在1966年提出的建議。當時的目標是在勞動力市場上找到一席之地,從而確保因技術變革而流離失所的工人不必遭受長期失業的恐慌。
第二個優先事項是修訂知識產權法,確定如何分配技術進步的回報方面發揮著核心作用。不幸的是,正如史丹佛大學的克爾茲(Mordecai Kurz)指出,美國的知識產權法已經發展到阻礙創新和加劇不平等的方式,同時傷害了消費者和工人。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不斷延長專利和版權保護期限,有效促進政府批准的壟斷。這造成瞭如此混亂,現在實際上兩黨支持回滾知識產權保護。但是,雖然減少知識產權保護的持續時間肯定會有所幫助,但這並不能確保公平的經濟。為此,我們需要消除目前扭曲經濟的大多數創新者租金。
為此,政策制定者應優先考慮公共資助的創新,其成果將是免費的並且可供所有人使用。正如倫敦大學學院馬茲卡托芙(Mariana Mazzucatoof)提醒的那樣,國家曾經在創造新市場和資助基礎研究方面處於領先地位,需要再次承擔這一角色。
透過建立技術變革的公共利益,政府可以確保創新使許多人受益,而不是少數人。例如,雖然許多私營企業僅使用人工智能來提取租金,例如通過數字營銷,這種強大的技術也可以用來減少工傷的發生率,提高工作質量,提高生活水平。
共同承擔
政策制定者要考慮的另一個想法是所謂的「工作分擔」。1930年,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預測,在一個世紀內,「3小時輪班或(每周工時)15小時」就足以滿足社會需求。然而今天,我們仍在努力工作,甚至效率低下。
但並非都是這種情況。
透過減少工作時間,可以更均勻地分享工作,並且在經濟衰退和轉型期間,工人可以繼續工作。事實上,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德國企業暫時減少了工時,不是解僱工人,失業率實際上有所下降。在美國,26個州已經開展了某種形式的工作分擔安排,目標是擴大全國實施。
最後的優先事項是高等教育。
在過去20年中,擁有大學學歷的工資幾乎不變,但仍遠高於僅接受過中等教育的工人。此外,即使是高度認證的工人,收入也開始停滯不前,就業機會也在減少中。
顯然,教育和培訓並不是所有勞動力市場困境的銀彈。然而,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對經濟和民主都至關重要,這意味著提供勞動力的負擔應該透過普及的免學費高等教育來分擔,不是以壓榨學生產生債務。
這份政策構想清單並不全面。
許多其他干預措施尚未提出,例如加強集體談判的措施,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史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指出的那樣,美國最高法院最近在《Janus控告美國國家聯合會》(Janus v. American Federation of State, County, and Municipal Employees)的判例中進一步破壞了這種干預措施。
我們還應該探索如何阻止矽谷龍頭(們)的市場支配地位,並將個人數據的巨大利潤社會化,目前這些數據由少數幾家公司收購。
雖然不是進行技術革命,但仍應繼續經歷技術變革。部分創新將不可避免地破壞一些工作,這沒關係。畢竟,我們應該想要破壞經濟中的不良工作,包括那些時薪低於15美元的工作。
但是,對於提供廣泛共享利益的技術,政策制定者必須改變遊戲規則。在一天結束時,我們不應該害怕機器人,反而應該擔心各國領導人會不願為公益事業而戰。
(原標題為《No Robo-Apocalyps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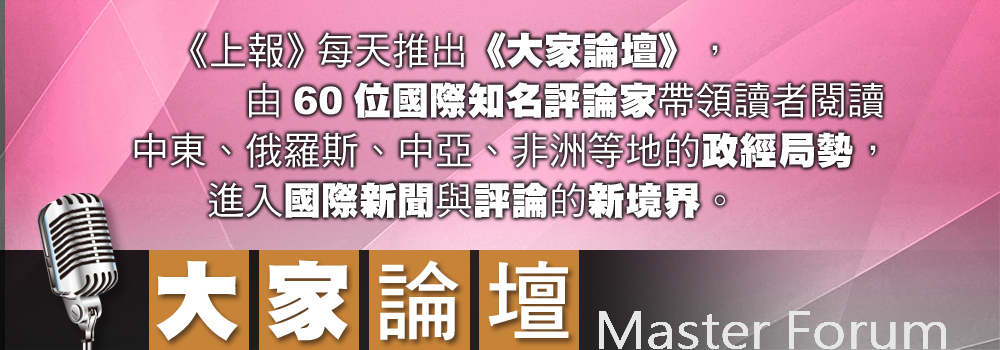
1000x200_2.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