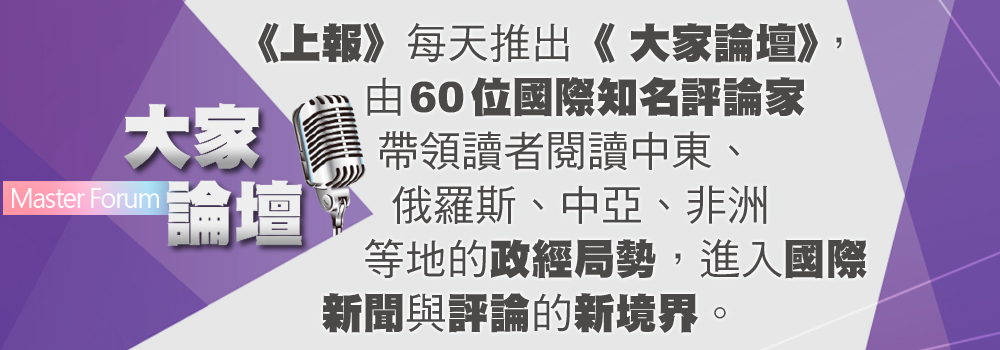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沈榮欽專欄:統戰怎麼做 —— 初學者須知 2024-12-16 00:02
- 最新消息 海基會要蔣萬安救富察 北市府:別甩鍋給地方 2024-12-15 19:50
- 最新消息 俄烏兩軍都在改造步槍 盼為抵禦FPV無人機的最後絕望防線 2024-12-15 19:00
- 最新消息 富邦金控攜手臺北馬拉松邁向永續未來 Run For Green™計畫提前達標 跑者領樹超過10萬棵 2024-12-15 18:53
- 最新消息 王齊麟向李洋道別 「麟洋配在球場結束了,但會留在粉絲心中」 2024-12-15 18:33
- 最新消息 【反登陸火力】捷克輪型自走砲曇花一現 推銷多年仍未獲官方背書 2024-12-15 18:32
- 最新消息 【反登陸火力】A7自走砲因遠距打擊順延 陸軍啟動建案納2026年預算 2024-12-15 18:30
- 最新消息 鼎泰豐小籠包軟實力最強 《外交政策》讚與台積電晶片同為台灣象徵 2024-12-15 18:00
- 最新消息 男師虐童遭解聘終身不得聘用 怒告校方、教育部被判敗訴 2024-12-15 17:45
- 最新消息 南韓代理總統與拜登通電話 強調依憲法行政、美韓同盟牢不可摧 2024-12-15 17:40


巴蘇
● 康乃爾大學經濟學教授
●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
即使處於最佳狀態,人類仍不擅於評估風險。當陌生的傳染病大流行,人們緊張又被隔離,且死亡人數不斷攀升,風險感知會更加失準,因為恐懼往往會勝過理智。而這就是政策失當的原因。
可以肯定的是,人們不應該低估新冠肺炎所帶來的危險。義大利、西班牙和美國的例子,尤其顯示了拖延防疫行動會導致大規模的感染及死亡。
但是盲目的恐慌沒有任何幫助。
在許多國家,特別是開發中國家,失當的政策所帶來的風險比起益處還要多,例如:經濟困難、糧食短缺、普遍焦慮。明智的施政會需要領導者及公民看得更遠。
新冠肺炎確切的死亡率難以得知,但計算死亡人數要比計算感染人數還要簡單,因為後者需要大規模的檢驗。從死亡數據來看,很明顯的,對多數人而言,也就是那些非高齡族群也沒有併發症的人,死亡的風險仍非常低。在多數的開發中國家,交通事故的死亡機率比新冠肺炎高上許多。
在印度,每年有超過15萬人死於交通事故。
大多數的人在高速公路上開車不會緊張兮兮的,但是自疫情爆發以來,他們卻連走出家門都害怕。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的研究所示,心理學中關於「凸顯性」的大量文獻能夠幫助我們了解這個情況。
先假設你想要買一輛最安全的汽車,你可能會閱讀所有型號的安全性數據,例如:每一萬輛車在道路上發生多少次電子或機械故障、車禍、死亡事故。最後,再選擇事故率最低的那種型號。但就在你打算買車的前一晚,你跟一個朋友見面,他跟你說他的表親就是開那型號的車,結果在他剛買完車的那一周,車子打滑發生事故,他就受了重傷。
數字本身的呈現方式也可能讓人們誤讀。
如果有一張列表顯示所有事故及事故車輛的型號,某個牌子的事故次數可能會遠比其他廠牌多,但其實這也只是因為這個牌子的使用者眾多。事故率固然比事故總數更重要,但是其中細微的差別可能被忽略,尤其當恐懼左右了人們的選擇。
目前,新冠肺炎的數據也帶來類似的狀況。
近幾周來,全世界的人都關注著美國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數已穩定地上升至將近7萬人。這個數據當然相較比利時(8000人)的死亡人數少。但是每100萬人中,比利時的死亡數(略低於8000人)遠遠超過美國的死亡數(大約2120人)。截至目前,比利時人死於新冠肺炎的機率,是美國人的3倍。
北美、歐洲的死亡率與非洲、亞洲之間的差距甚至更為明顯。
在歐洲,一個人死於新冠肺炎的機率,通常比非洲或南亞高2000倍至4000倍,即使只考慮疫情較不嚴重的歐洲國家,差距仍然十分明顯。在德國,新冠肺炎的致命率仍比印度高100倍。
在印度,貧窮所帶來的風險,卻遠遠高於德國。然而,許多發展中國家非但沒有把這些因素考量進去,而在制定政策時,只著眼於新冠肺炎所帶來的超顯著因素(ultra-salient),卻忽略了新冠肺炎的致死率其實很低。
這種措施的代價正在提高。
在非洲及南亞的新興經濟體中,長期的封鎖,並不是在拯救生命與拯救股價之間做取捨,而是選擇拯救少數人免於因新冠肺炎失去性命,卻犧牲更多的人,讓他們陷於貧困、饑餓甚至死亡。
部分人會說,這個結論為時過早。
斯里蘭卡、印度、肯亞和奈及利亞的死亡率目前看來很低,但可能明天就面臨大規模的感染,決策者一定要預測未來趨勢,並及早採取行動以減低風險。
但是目前仍然未知南亞、非洲的疫情趨勢,是否會與歐洲、北美的軌跡雷同,所有非洲、南亞國家跟北美、歐洲國家如此鮮明的差距,代表可能有其他因素影響新冠肺炎的傳播。其中一個可能,是非洲、南亞國家廣泛施打卡介苗(以預防肺炎),因為肺炎、瘧疾在這些國家很常見。
這並不代表開發中國家的領導人不需要防患未然,特別是考慮到我們對於新冠肺炎仍不甚了解。他們當然不能像巴西總統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一樣,即使屍體堆積如山,仍忽視及低估疫情的風險。
但是領導人必須避免適得其反,也要避免被恐懼支配。
相反地,他們必須根據數據及專家的意見,做出艱難卻考慮周全的決策;隨著資訊、事態,去改變施政;並且要讓人們了解情況。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法國總統馬卡洪(Emmanuel Macron)都是這種領導的楷模。
公民也該如此。
為了要保衛我們的家園,必須採取一切適當、可行的公衛預防措施,例如:戴口罩、減少肢體接觸,尤其是面對較脆弱的族群。然而,一定要意識到,這類措施有很大一部份不只是為了自己,更是因為在面臨傳染病時,人類需要擔負起自身的社會責任。
(翻譯:吳思潔,責任編輯:簡嘉宏)
(原標題為《Who’s Afraid of COVID-19?》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