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郝明義:只有賴清德總統能完成的歷史任務 2024-12-13 00:02
- 最新消息 麟洋配苦戰64分鐘遭丹麥組逆轉 年終賽小組賽1勝1敗 2024-12-12 22:18
- 最新消息 阿塞德垮台 日經專欄:習近平還記得2017年與川普的那場「鴻門宴」嗎? 2024-12-12 21:58
- 最新消息 中國軍演危機解除 參謀總長解除各級應變中心 2024-12-12 21:55
- 最新消息 台積電效應發威 去年赴美工作人數12.8萬創新高 2024-12-12 21:38
- 最新消息 川普登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 2016年獲選後再領風騷 2024-12-12 21:06
- 最新消息 大法官人事審查國民黨挑明立場 堅決反對「實質廢死」 2024-12-12 21:05
- 最新消息 吉伊卡哇明年 1 月現身高雄愛河灣!魔法吉伊卡哇快閃店月底插旗台北華山 2024-12-12 21:00
- 最新消息 台鐵票價凍漲近30年 陳世凱:農曆年後討論是否調整 2024-12-12 20:37
- 最新消息 【大法官人事案】罵王義川蠢到爆、諷管中閔是瘋老男人 劉靜怡「狂言」成質詢焦點 2024-12-12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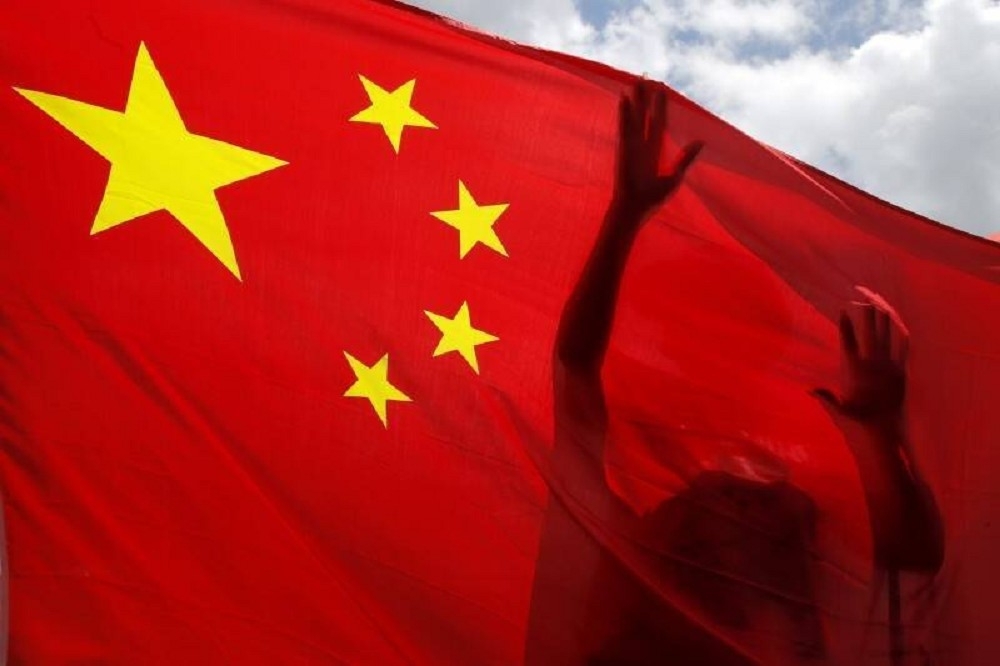
在中國當記者,很長一段時間會搞不清什麼才是真實,有些宣傳內容則是誇大其詞,而每天一篇稿子的kpi還像鞭子一樣在身後抽,催得人來不及細想,只能模仿和複製那些陳詞濫調。(美聯社)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從在市政府門口等一輛公務車開始的。
下午兩點開始視察活動,時間剛到,政府大廳的玻璃旋轉門打開,幾個人迎面出來,最前面的那位很顯眼,是市長,已經提前在報紙上見過。
公務車像輛小型麵包車,但有自己的規格和制式,上車後市長坐在最前排的位置,那個帶了桌子的椅子。桌上有水、紙筆,每個座椅背後的網籃裡也放了瓶裝的礦泉水。等領導們全部上車,我跟著電視臺的攝影大哥迅速溜到最後排,沒人跟我們打招呼,甚至沒有一個眼神,仿佛我們是空氣。
這是次例行的市長檢查,第一站,到市里一處水產市場視察安全衛生。到地下車,市場的幾位負責人已經站在門口迎接,邊走邊跟市長介紹情況。市長在一些海鮮攤位前駐足,或者走進店裡跟店主交談。一排排海鮮池裡冒起不斷升騰的氣泡,把店面襯得更窄。一群人跟著魚貫進入,我拿著筆和筆記本緊跟市長左右,試圖聽清他們在說什麼。
從第一家店出來,攝影大哥叫住我,指了指市長:「別靠他太近,你倆都要同框了」。一回想我剛才的舉動,大概耳朵都要貼到了市長臉上。
後來我才知道,其實不用仔細聽,事後市長秘書會提供通稿,哪怕沒有文字材料,也會有詳細的視察流程、位址、每個點的視察內容,如果是走訪個人或企業也會有相關資訊。寫這樣的程式化通訊稿有固定套路,只要記清楚地點名字,按照先後順序一羅列,加上一些連接詞、套話就能完成。等審核通過,登上第二天日報頭版頭條。
我忘了那天還視察過什麼地方,只記得跟著人流上車、下車,兜一圈回到市政府門口。不過我工作的地點不是政府部門,而是距此五分鐘路程的報社。
政府大樓搬遷到新城後修得很氣派,作為市級媒體自然挨在旁邊。25層高的報社坐落在新街區,和旁邊十幾幢銀行和公司大樓比肩。到了夜晚,刻有報社名字的紅色燈箱在樓頂閃光,像茫茫黑夜的一個座標。
那是2020年。在做這份工作以前,在我出生的家鄉生活了十幾年也不知道本地市長和市委書記的名字。而在報社,四大班子領導人的名字排序被貼在每個人的辦公桌上,新聞稿裡的頭銜和名字先後順序、不同人的版面位置有講究,比如市委書記和市長的新聞都要放頭版,但市委書記的要在更上面,弄錯一點都是重大事故。
第一次採訪以跟市長貼太近而尷尬告終。其實我本沒有資格去跟市長活動,只是剛入報社還在見習期,沒被分配條線,部門主任暫時讓專跑市長活動的記者帶我。
我被分到了日報的時政要聞部,除了主任和一個即將退休的老記者,部門9個人裡,只有跑市長活動的A記者是男性。三十出頭的年紀,能跑市長活動,意味著他已經是潛在接班人。其他記者沒什麼異議,都說:「畢竟他是男的」,潛臺詞是這麼重要的活兒當然要給他。
可接班人的位置並沒有留住他。我來後不久,他就跳槽去了當地資金雄厚的旅遊開發公司做宣傳。大家又很理解地說:「畢竟他結婚了,還要養家」,似乎報社這樣的工資水準開給女員工可以,但對男員工來說卻不夠。
部門裡只有我一個90後,其他記者都是本地人,或者是從上大學開始就留在這裡。而經歷考研失敗和疫情時期的艱難求職,我誤打誤撞來到這裡,像是經歷一場放逐,墮入一張陌生的社會關係網,而對於媒體的祛魅從此刻才剛剛開始。
後來我又跟了很多次市領導會議。
會議總是很多,流程相似。進門領材料,聽領導念材料,領導念完了就講幾句鼓勵大家工作加油幹之類的話,大家鼓掌,會議結束。
有一次舉行專題學習會,會議廳裡黑壓壓坐滿了人,黑衣黑褲、公事包,在一眾平頭裡偶爾能看到幾個長髮,女士也穿著黑白灰。
幾個領導坐在台前,對著話筒和講稿輪番滔滔不絕。戴著白手套的後勤人員在中途端著保溫壺進來續茶,一次、兩次、三次,會議結束。一開會就是坐一上午或者一下午,不得不說領導的膀胱真的很優秀。
電視臺的攝影大哥在會議開始前就來架好了機器,拍到幾個領導講話的大頭像和會議現場的畫面就準備走。
「明天出吧?」他走之前拍拍坐在最後排不起眼位置的我。日報的稿子會比電視新聞出得早,他想用我寫的文字配畫外音。我點點頭,裝作已經聽懂這個會在講什麼的樣子。
其實我在走神。那些空洞而宏大的發言像水汽,經過話筒傳出來,剛飄到空氣裡就蒸發了。我看到現場不少人和我一樣,不是在悄悄低頭看手機,就是昏昏欲睡。
落到紙面,會議的內容就成了:「xxx指出要找准工作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切入點、結合點、著力點,聚焦大事、關注實事、緊盯難事,深入調查研究,拿出更多有價值、有分量、有見地的履職成果。」好像寫了很多,又感覺啥也沒寫。
主任說,日報的稿件「要站在全市的高度」。剛開始我寫不出這些冠冕堂皇的話,資歷深的記者教我,從以前類似的稿子裡「借鑒」,有的甚至直接抄過來也不違和。久而久之,大腦也像經過自我學習和進化的AI,儲備了大量詞彙——凡要說明事情很重要必是「大考」、凡是檢查什麼設施就是「大體檢」、凡加大力度就是「重拳出擊」、聯合整治行動就是「聯合作戰」。「提升」「促進」「推動」「齊發力」「高標準」「嚴要求」,這些詞放到哪裡都是「萬金油」般的存在。
好像寫八股文,我開始懷疑這份工作存在的意義。現在還有誰會從報刊亭買一份報紙來讀呢?就算有,這個四百字的豆腐塊也沒什麼好看的。學生時代被那些特稿作品和精彩的採訪故事感染,沒想到等自己當記者時只能被框定在既有的敘事邏輯裡,動彈不得。
我以為等我有了條線之後就能寫更多有現場、有採訪的稿子,而在被分配了條線後,才發現面臨更大的難題——找選題。
日報出版像車輪一樣滾滾迴圈。每天下午三點交稿,五點報第二天的選題,第二天繼續採訪,周而復始。稿件數量和工分、工資直接掛鉤,報社還會根據工分高低給每個記者排名。貼在公告欄裡的排名表像學生時代貼在教室黑板旁的月考成績單,多看一眼都會心悸。
我被分配到的條線是交通。從前只聽說過跑社會新聞、醫療、突發的記者,交通?我一臉茫然。
主任給了我一些條線上對接人的聯繫方式,都是交通局下屬部門裡宣傳科室的負責人。公交集團、公路事業發展中心、運管處、港航處……好多部門,我花了很長時間才厘清交通局的組織架構和這些人之間的親疏關係。
從前我以為記者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實際上我只是負責宣傳政府事務的乙方。就算日報的調性和市場化媒體不同,按理說我們和政府的關係至少是合作,負責宣傳的人需要日報去推廣他們的工作,我們也需要他們提供線索寫稿。但最終定性定調的是他們,給通稿、審稿的也是他們。
有段時間交管部門開展非法營運整治行動,整整一個月都在抓違法網約車和無證貨運車,行動代號響噹噹:春雷行動。我跟著執法人員到景區門口抓黑車,正好碰到輛私家車車主接私活。在稿子裡,我寫在執法人員的教育下,被抓司機後悔不已,承認自己的錯誤並接受了處罰。實際上他當時罵罵咧咧,後悔的可能只是自己運氣不好被發現了。等到全市開展船舶碼頭專項整改,在碼頭,那些排汙量超標的船舶被起重機吊起,送到專門的工廠拆除,它們最終變成了一串彰顯整改成果的數字。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搞不清什麼才是真實,這些宣傳的內容總是誇大其詞。而每天一篇稿子的kpi像鞭子一樣在身後抽,催得人來不及細想,只能模仿和複製那些陳詞濫調。就算我想寫得稍微有點新意,也會在提交審核後被全部刪掉。上學時我們還在討論記者是否應該拒絕讓採訪物件審稿,工作後才發現事前審稿已經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
報導這些事情也有節點,要麼是剛開始,報導活動「打響第一槍」;要麼是中途,寫出現的典型案例;要麼是行動結束,歌頌成果。除了這些時間節點外,很多時候我都找不到選題。
小城市的新鮮事太少了,要獲得資訊,只能依賴政府部門。為了和條線上的人搞好關係,每週一早,我先在微信上跟好幾個宣傳負責人打招呼,開頭卑微地叫聲「姐」,然後小心翼翼地問:「這周你們有啥要重點宣傳的嗎?有沒有可以報導一下的?之前說的xxx有沒有新的案例/進展呀?」我覺得自己像個乞丐,到處乞討:給點吧給點選題吧。
有一次和晚報、電視臺跑交通的記者一起吃飯,說起交通部門裡的G姓對接人總是很磨嘰,審稿慢、對記者愛答不理,他們叫他:G娘娘。「真不好伺候」,大家感慨。
不好伺候的不只是部門裡的人,還有報社領導。G娘娘們總是希望我盡可能用較長的篇幅來寫他們的工作成效,但主任有自己的判斷,他覺得不重要的就會讓我把交上去的稿子砍掉大半,還指責我寫超了字數,一般一篇稿子只能寫四五百字。而G只會覺得我不配合,下次就不給我好臉色。對於那時初入社會的我來說,比寫稿更難的是處理這種關係,感覺被夾在了中間,不知所措。
其他記者手裡一般都有兩三個條線,主任只給了我交通這一條,是之前離職的男記者A遺留的。他覺得我資歷淺,美其名曰鍛煉我發掘新聞的能力,說:「你單跑這一條都不一定有A之前跑得好」。
有記者私下對我表示同情:「這樣你怎麼吃得飽呢?」但當時我唯唯諾諾,覺得這事兒不合理但也不敢反駁,甚至覺得找不到選題或許真的是自己的問題,是不是還不夠努力?是不是太內向,還不夠主動去問?還為主任操起心來,畢竟一個蘿蔔一個坑,其他條線都有人跑了,讓誰拿出來都不好。
那時的我也還以教科書上的新聞價值為標竿,沒有參透日報的選題要在標竿之下找。
有次專跑房管和住建條線的S記者報了一個「去工地參加市住建局組織的智慧工地VR虛擬觀摩活動」的選題,主任讓我和她一起。
我想智慧工地應該非常高大上吧,可到了一處住宅工地現場,看到VR體驗裝置被放在臨時的活動板房裡,房間只有三十平左右,門打開,黴味撲面而來。負責人調試了很久的設備,打不開。草草參觀一圈,只花了不到10分鐘。看來只有在活動時的工地才是智慧工地。而且負責人透露,活動早在一個周前就已經舉辦了,可S記者在第二天即將發的稿子上寫了「昨日」。
我好像窺見了她的稿件數量總是遙遙領先的秘密,活動舉辦時她來不及采,後面為了多報題又找這件事來湊。當時我們還不熟,採訪結束的返程路上她才告訴我,這樣的新聞她一般不會去現場,拿相關方給的通稿改一改就能交差,這樣她一天能寫兩篇。「一篇豆腐塊文章五百多字才賺幾十塊錢,去現場油費都不夠的」,S說。
不止S一個人,但凡能拿到通稿,記者們能不去現場就不去現場,只有主任被蒙在鼓裡。
而小事經過「包裝」,也能成為選題,登上報紙。像冬天公交司機自掏腰包給乘客座椅裝上棉墊、清明假期汽車票開啟預售方便祭掃這樣的小小「正能量」,原本我不覺得是值得報的選題,沒想到寫出來後主任很滿意。
原來但凡是誇有關部門做得好的,哪怕再小,都可以見報。後來看到機場入口處新增了些綠植假山,我學會了聯繫機場負責人瞭解情況,寫了一篇《機場園林式景觀扮靚「城市視窗」》。因為機場是「城市的名片/視窗」,綠化升級改造就成了「大事」。
至於負面消息,則完全沒有刊登的餘地。剛來報社時本地發生過一起學校老師貪汙學生伙食費的事情,紀委已經定性,我去問A記者,這件事我們會不會寫,哪怕只是說清事情的前因後果,再摘點通報上的話。他對我的問題感到驚訝,說:「以宣傳部門工作和正能量為主」。
我好像沒眼力見兒,參不透這些不言自明的規則,後來才學會無視,仿佛這樣的事從沒發生過。
在評選全國文明城市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我市肯定能評上,結果遭遇滑鐵盧,名單公佈了,全省只有本市不文明。
消息出來當天夜班編輯驚呼:「明天頭版還做啥啊,這就是今天最大的新聞!」辦公室裡一時間充滿了快活的空氣。當晚網易新聞發了篇稿子,標題特別損:xx省除xx外的xx個設區市均獲得全國文明城市榮譽稱號,連結在記者群裡廣為流傳。
各個單位紛紛進行文明城市建設整改提升工作部署。之後是各部門領導連夜走訪巡查,記者們都被要求去報導積極整改的成效。有天一位元記者發了條朋友圈調侃:XX花園的狗,你可知道今晚有多少人為你加班。
此前已有流言傳開:這次沒評上文明城市是因為一條狗。有個居民晚上遛狗沒牽繩,狗竄出來和前來視察的檢查組領導迎面撞上。結果第二天我們就接到通知:朋友圈禁止發佈、評論、轉發跟狗有關的內容。
那兩個星期跑市政條線的記者忙瘋了,連我條線上也開展了一個「評選10輛文明樣板計程車」的活動。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整件事的荒謬,日報像個篩檢程式,負面新聞要麼被自動過濾,要麼在裡面滾一圈,再以非常正面,甚至是驕傲的語氣被報導出來。
既然稿子的內容、風格我都無法決定,也沒法像S記者那樣坦然地改通稿,後來我對自己的要求僅僅是,至少要去現場。
五一勞動節前,照例要寫一批勞模候選人。在眾多人的事蹟材料裡,我看到一個90後的女生——全國少有的地鐵挖掘盾構機的女司機。
這是我想寫的人。我打電話到她所在的建築局,負責人告訴我她正在鄰市建地鐵的專案工地上,最近回不來。一位元記者建議我拿她的事蹟材料改改交差,內容已經夠多了。我不死心,沒過幾天又問了一遍,正好趕上她那天下午回本市。
建築局裡擺著一台還沒投入使用的盾構機,她個頭小小的,坐在只夠剛剛轉身的3平方駕駛室裡,向我展示怎麼操作這個五百噸的大塊頭,把一條地鐵隧道挖通。每天有12個小時她都要待在不通風的地下,夏天裡面的溫度到了39度。冬天又冷,隧道越挖越深,午餐從地面上送下來,吃上時已經涼了。
她說最大的困難是無法上廁所,男生可以就地解決,她只能選擇少喝水,這也是為什麼這項工作很少有女孩做。因為喜歡數學,她學了土木工程,不服氣別人說她幹這個「堅持不了一個月」,結果現在成了老師傅口中的「大俠」。
主任大概覺得這個選題比較獨特,當晚就叫我寫出來,第二天作為勞動節專欄的第一篇發表。等到夜班編輯打電話找我確認最後的標題,已經是晚上11點半。
即使是勞動者的故事,主題也必須是宏大的:她有「工匠精神」,希望成為一流的城市軌道建設者。這些被加上的話,把她拔高到了偉光正的地步。
其實我更想寫的是她遭遇的無奈與選擇,如何在一群男性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可惜立體複雜的人在日報從來都不存在,我在日記裡寫:「我不喜歡新聞裡的她,我喜歡真實的她」。
去了現場,結果呢?反正最後的成稿也跟事蹟材料如出一轍。那些不去現場的記者,我原本以為她們只是懶,只圖省事多賺錢,可是不是最開始她們也是去現場的?只是比我提早發現了這個真相。日報真是個讓人不自覺就變成自己討厭的人的地方。
不過跟八股文一樣的會議稿和四百字的豆腐塊比起來,這已經是我在這份工作裡寫得比較滿意的稿子。總編第一次誇我寫得好。那時我還有很深的好學生心態,哪怕討厭這套評價體系,也希望得到認可,這朵「小紅花」讓我開心了很久。
而這樣的故事頂多也只能寫1200字。因為她們只是「小人物」,能被頭版頭條報導的,從來都是政府的重點工作和那些上頭的指示。
在報社面試時,我就被問到「你如何看待長三角一體化」,接手了交通條線,但凡和「長三角一體化」掛鉤的消息就可以大書特書,如果寫少了還會被主任罵。聰明的記者可以做到「聽風就是雨」,把還沒譜的事兒寫成大稿。更靠前的版面、更高的稿件評級、更多的稿費似乎都在誘惑我們:快誇大事實吧。
有段時間上面發了一個珍惜糧食的宣導,過幾天本市報紙上就全都是關於光碟行動的報導了。正好部門聚餐,圖片記者馬上想到擺拍一張我們吃飯光碟的餐桌。我驚訝這也能行,標題就是「‘光碟行動’正成為x城就餐新風尚」,真的成風尚了嗎?看圖片是成了。
後來我已經能大概判斷哪些事情是報社青睞的選題,忍著噁心寫那些不想寫的東西,更多的還是焦慮,有時候做夢會夢到自己在宣傳科的辦公室裡點頭哈腰。每次能到點報題,都有一種感覺——又能活過一天。雖然不知道後天的選題在哪裡,但至少現在不用愁了。
我會期盼小長假的到來,不是因為放假,而是每到假期我就能去高鐵站、機場走一圈,拿到一個交通樞紐客流量又創歷史新高的資料,寫寫現場人流的場面,填上第二天的版面。在節假日開始前,還可以先把計畫增開車次、預計客流情況寫一遍,這樣又報出了一個選題。
2020年的春節前夕,我寫了8篇春運「故事」,那些典型的、像小品一樣的故事:火車站送給旅客對聯福字、90後高鐵檢票員手繪防疫提示卡、高鐵客運員提供暖心服務受助者記掛兩年專程來道謝、過年來當地旅遊的遊客對本地景點稱讚有加……
那段時間一旦報不出選題,主任就說:「去火車站看看」。我委婉地表達已經寫得夠多了,內心其實在呐喊:這種新聞到底有誰愛看啊。他只是說:「你不要預設,去了才知道」。
記者們大概都苦選題久矣。S記者跟我說過一個比喻,我們記者其實跟外賣小哥一樣,只是看起來高級一點,基本工資都很低,靠計件工資為生,「甚至還不如送外賣的,至少人家有單可派,我們連單都要自己找」。
直到有一周,即將退休的那位元男記者有事請假,我暫時接手了他跑的條線。才發現原來不是所有條線的選題都那麼難找,資歷最深的人已經牢牢地把最輕鬆的活握在了自己手裡。
他的條線上有好多會,那一周我過得有多舒坦,不用再求爺爺告奶奶地找選題,每天都被會議通知安排得明明白白。上午不用去報社,聽完會找個咖啡店看書或幹自己的事,中午回報社食堂混一頓免費的午飯。有時候會議在市政府下屬的酒店開,還能蹭到一頓豐盛的自助餐。下午寫稿用不了一個小時,寫完上傳採編系統、排版好發佈到App,然後坐等下班,五點鐘一到走人。
我再也不覺得跑會議是件痛苦的事了。以前我懷疑為什麼有那麼多無聊的會,媒體為什麼要報這些無聊的會,但那周我理解了什麼是「存在即合理」。要是沒有會,有多少公務員要失業,有多少記者半夜為選題想禿了頭。比起編空話的新聞稿,還是會議稿的空話更直白、更好編。
報社的環境像溫水煮蛙,痛苦忍受得多了,要麼人會變得遲鈍、麻木,直到最後沒有知覺;要麼只能因為無法忍受而出走。
從畢業時拖著行李來到這座陌生的城市,經歷一整個春夏秋冬,在第二年的幾乎同一時間,我辭職了。分離總是在夏天,在報社經歷的種種都像一場夢,除了報紙上的一個個署名,在這座城市我什麼都沒有留下。
房租提早到期,離開的前幾天,我到一位同事家暫住。我們同期入職,經歷相似的心路歷程。在我離開的最後一晚,我們做飯,在客廳看完了整場嗶哩嗶哩的畢業歌會,好像回到了大學宿舍。但一切都已經不同了。
從前我認為成為一名調查記者才是這份職業的最高榮譽,而在日報,更多的是作為打工人的記者日常:改通稿、報小新聞、寫宣傳稿、等待隨時可能的斃稿。我試圖理解這套規則,學習一些說話的藝術,聽懂官腔背後的真實意圖,但無論如何都像穿上大人衣服的小孩,只是在拙劣地扮演成年人。也開始明白「找選題—採訪—寫稿—發佈」不是一個清晰的閉環,其中有太多不可控因素,新聞是各方博弈的結果。
如果我對這份職業沒有那麼期待,或許就不會那麼失望。而這份失望更多地轉向向內的攻擊,先是自我懷疑,然後是不甘心。我以為只是黨政機關報如此,如果能去更一流的市場化媒體就會不同。當時我能想到的途徑只有考研,去媒體雲集的大城市,實習,然後留下來。辭職後脫產二戰,還是以失敗告終。
不得不繼續投簡歷找工作,意外收到來自一家知名市場化媒體的橄欖枝。短暫的開心過後,更多的是冒名頂替者綜合症作祟:為什麼是我?帶著這種強烈的不配得感戰戰兢兢工作五個月,發現環境已經逼仄到讓行業內所有人都感到窒息的程度,而內部的人也不過是系統裡維持機械運轉的一顆螺絲釘。
在日報工作的時候我很擰巴,既討厭報社的這套運轉規則,卻又想做好。一直以來在應試教育的邏輯下成長起來,即使面對不喜歡的科目,也想要拿個好成績。我努力完成派給我的工作,沒想過去質疑這是否合理,就像在課堂上點頭如搗蒜的好學生。每天晚上都去附近的公園,邊踱步邊反問自己:為什麼會在這裡?為什麼要寫這種報導?做這些事有什麼意義?等到後來能完全適應,也寫出了被認為是「好」的稿子,但這樣的疑問還是沒有停止。
後來我離開媒體,再也沒有幹過像報社那樣輕鬆的、能在五點前下班的工作,再沒見過工作日傍晚的夕陽,租住在破舊的城中村,附近也沒有公園,卻沒有那麼痛苦了。或許我已經不會像從學校剛踏入社會時那樣,一看到黑白不明的事情就反應過激,也終於擺脫了優績主義的思維,自由地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那家知名媒體,後來在年末評「十佳員工」,有位入選記者的頒獎詞是:「入職三年半,他連續三年刷新x報社文字記者工作量紀錄,先是前輩的,後是自己的…又好又多不是夢」。
以前我該有多羡慕,現在心裡居然鬆了口氣:「對牛馬的最高評價也不過如此了」。我不會再跟著這套規則玩了,也不想再接受這種認可。
我還是很喜歡這份職業,採訪和寫作本來應該是不被束縛的。跳脫出工作本身,我想抓住和珍藏那些人與人聯結時心靈相通的時刻、因為未知而激起的好奇心和還想說點什麼的表達欲。
※本文轉載自《中國數字時代》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趙麗穎與《玫瑰的故事》林更新爆熱戀 她帶兒子看煙火他「這穿搭」現身放閃
- 趙麗穎與《玫瑰的故事》林更新被抓包穿情侶裝 兩人隔空示愛3證據曝光全網沸騰
- 張若昀《慶餘年》第二季流量奪冠成劇王 他開2千萬跑車因「這舉動」形象全毀
- 【有片】中華隊球員「無敵星星」吊飾哪裡買?博客來明日早上再次開放預購
- 《長相思》檀健次開唱勁歌熱舞嗨翻 卻被抓包在台上做「這件事」超噁心掀罵聲
- 《永夜星河》虞書欣新劇停拍3天劇組全換人 官方海報獨厚她卻沒男主角內幕曝光
- 譚松韻《蜀錦人家》與鄭業成吻戲被刪光掀眾怒 2敗筆熱度慘輸孟子義新劇《九重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