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toggle- 最新消息 俄烏兩軍都在改造步槍 盼為抵禦FPV無人機的最後絕望防線 2024-12-15 19:00
- 最新消息 富邦金控攜手臺北馬拉松邁向永續未來 Run For Green™計畫提前達標 跑者領樹超過10萬棵 2024-12-15 18:53
- 最新消息 王齊麟向李洋道別 「麟洋配在球場結束了,但會留在粉絲心中」 2024-12-15 18:33
- 最新消息 【反登陸火力】捷克輪型自走砲曇花一現 推銷多年仍未獲官方背書 2024-12-15 18:32
- 最新消息 【反登陸火力】A7自走砲因遠距打擊順延 陸軍啟動建案納2026年預算 2024-12-15 18:30
- 最新消息 鼎泰豐小籠包軟實力最強 《外交政策》讚與台積電晶片同為台灣象徵 2024-12-15 18:00
- 最新消息 男師虐童遭解聘終身不得聘用 怒告校方、教育部被判敗訴 2024-12-15 17:45
- 最新消息 南韓代理總統與拜登通電話 強調依憲法行政、美韓同盟牢不可摧 2024-12-15 17:40
- 最新消息 太可怕!花博公園化糞池「屎水噴出」畫面曝光 民眾怨:超級噁心 2024-12-15 17:34
- 最新消息 「最難訂牛肉麵」以後不能訂了 老闆宣布:全部只能現場排隊 2024-12-15 17:08

1000x80_10.jpg)
班阿米
●台拉維夫大學歷史學教授
●曾任以色列外長(2000.11 – 2001.03)
●著有《戰痕、傷口與和平》
2018年夏天以色列通過一項極富爭議的新「民族國家法」,聲稱行使民族自決權是猶太人獨有的權利,同時將希伯來語確立為以色列的官方語言而將阿拉伯語降級到一個特殊地位。然而,在多元化社會中強加某種同質身份定義的動力並非以色列所獨有,相反你在整個西方世界都可以看到—這對和平來說可不是個好兆頭。
在過去幾十年的快速全球化過程中民族主義其實從未真正遠離我們,只是不敵人們對更大經濟繁榮的寄望而已。然而近期對全球化的抵制—不僅出於經濟不安全和不平等,還由於對社會和人口構成變化的擔憂—引發了那種老一套種族民族主義的捲土重來。
這種趨勢在一些專家所謂的「記憶潮」或「紀念狂熱」中得到體現、強化:一些博物館、紀念館、遺址以及其他強調與當地身份和歷史聯繫的公共空間紛紛湧現。人們越來越渴望擁有一種特定且獨有的身份定義而非倡導多樣性。
白人表現得像是弱勢團體
在美國,白人越來越認定自己將成為少數民族—預計將在2045年實現的里程碑—並將此視為一種存續性威脅,並且往往表現得好像自己就是一個弱勢群體。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正是利用這樣的情緒去贏得支持,而他的共和黨如今依靠對不活躍選民的強力清洗,嚴格的選民身份法以及關閉投票站來讓少數民族投票更加困難。
與此同時,對歐盟開明價值觀支持也已受到侵蝕。有點諷刺的是,右翼民族主義政黨已經建立了一個大聯盟以提高自身在2019年5月歐洲議會選舉中的機會。
這些勢力對「身份政治」表示反對(同時又不斷對自認國家真正代表的白人群體喊話)。這種言論也得到了一些左翼和右翼知識分子的同情。比如里拉(Mark Lilla)和福山(Francis Fukuyama)這樣的評論家都表示多元文化主義和國際合作最後都不過是自由派精英的幻想。
同樣,長期以來一直譴責「超自由主義」的英國哲學家格雷(John Grey)試圖將英國脫歐投票—某種明顯的本土主義和仇外心理的爆發—歸咎於其上。在格雷看來,推動一個違背大多數歐洲人意願的「跨國政府」的歐盟應該對那些最惡劣形式民族主義的崛起負責。他堅稱抵制英國脫歐就等同於回歸到過去的黑暗歐洲。
歐洲仇外、極端民族主義復活
英國前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的一系列反恐法規是在2005年受基地組織啟發的倫敦自殺爆炸事件後頒布的,這也使他成為了第一個否定所謂超自由主義的西方領導人。如今,從川普政府,匈牙利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án)、波蘭實際領導人卡欽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的「非自由主義」,再到義大利民粹聯合政府身上都可以看到西方世界的這種否定。
類似以色列民族國家法所規定的種族民族主義長期以來一直是中歐和東歐政治的主要內容。血統和宗教—而不是公民身份—曾經是歐洲各國相互征伐時期的國家定義。在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的毀滅之後,該地區的許多國家都是通過大規模的種族清洗恢復了主權。
戰後的歐洲一體化未能使中歐和東歐19世紀末的多民族夢想成為現實,仇外心理、極端民族主義的幽靈已復活,反對德國戰後贖罪行為的極右翼德國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近期不斷高漲的支持率就是一個極佳例子。
西歐本該無種族民族主義
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的開明難民政策可能會成為德國贖罪政治的最後體現。同樣,在首先從未承認過罪責的奧地利,總理塞庫爾茲(Sebastian Kurz)的極右翼反移民聯盟已經準備好要終結歐盟的「去身份化」政治。
西歐本來應該沒有種族民族主義。這些現代民族國家都是沿著公民而非民族線路而打造,國家被定義為一個公民的社區。種族,膚色和性別從未被認為是全面且平等的公民參與的障礙。
此外,西歐在很大程度上是世俗的,而中歐和東歐的大部分地區(更別說美國)更有可能將其身份與基於宗教的道德秩序聯繫起來。有鑑於此,西歐激進民族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對恐怖主義和大規模移民的恐慌性回應,也是一場更為根本的轉型性危機。
西歐、北美正在發生民主衰退
那些北歐傳統道德超級大國更是如此。極右翼的丹麥人民黨和瑞典民主黨的崛起—發源於瑞典法西斯主義,以及他們對1950年代神話式白人瑞典的懷念—對歐洲有史以來最完美的社會民主模式構成毀滅性打擊。在這些民族主義者看來社會福利國家是不能取代民族認同的。
最近發表在《民主化》學報上的一項研究表明,目前全球自由民主的總體水平與1991年蘇聯解體後不久的記錄一致。正如福山所說,一場「民主衰退依然發生,但它卻集中在了在世界上更為民主的地區:西歐、北美、拉美、加勒比地區以及東歐。
鑑於這些地區對維護自由世界秩序的重要性,(白人)種族民族主義的興起很可能會引發嚴重後果。除非這些國家能設計出一種可以平衡自由民主價值觀和人們歸屬感的新方法,否則將走上災難之路。
(原標題為《The Disruptive Power of Ethnic Nationalism》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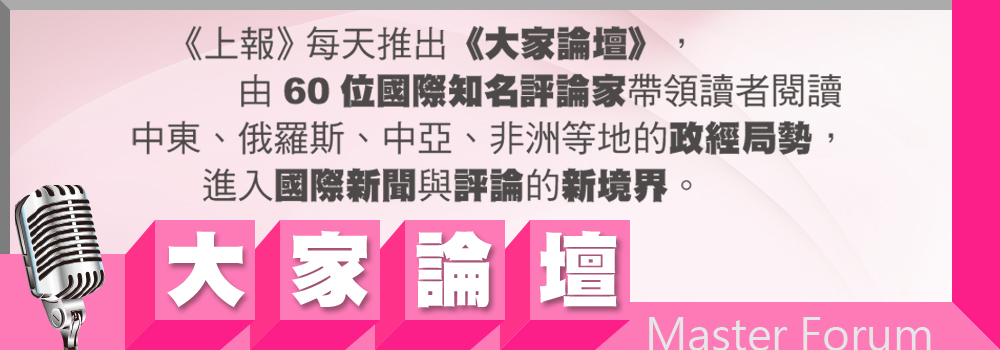
熱門影音
熱門新聞
- 【懶人包】勞動部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輕生 事件始末「時間軸、手段、調查結果」一次看懂
- 《繁花》胡歌睽違9年接演古裝劇竟被看衰 網推這位「台灣金馬獎影帝」比他更適合
- 張若昀《慶餘年》第二季流量奪冠成劇王 他開2千萬跑車因「這舉動」形象全毀
- 《蜀錦人家》譚松韻激吻鄭業成甜翻播放量破2億 他被抓包「親到滿臉漲紅」全網笑翻
- 《永夜星河》虞書欣新劇爆金主撤資風波不斷 《偷偷藏不住》趙露思哥哥演男配慘被換角
- 《九重紫》打趴《蜀錦人家》熱度奪冠 李昀銳戲外喊孟子義老婆兩人10大互動超閃
- 《九重紫》孟子義熱戀李昀銳口碑爆棚 她曾與肖戰搭檔演戲因「這件事」被罵到無戲可拍
- 黑夜君臨!《艾爾登法環》宣布 2025 年推出多人合作類衍生新作《Elden Ring Night Reign》

1000x200.jpg)








